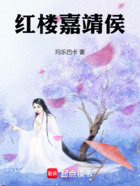
第25章 明亡于万历
“叔大何来迟也。”
“起的晚了,外边有没订到票的围成一片,挤进来可不容易。”
殷士儋、李春芳两位友人帮他占着空位,张居正就此坐下。
三人同科登第,又同入翰林,关系颇为亲近。
“这脂砚斋号称书坊,结果一应布置与茶书馆类似,楼上还有雅间,卖书的地方倒是没看见。”
“道是书尚未印好,先让大家试听一二。”
“试听还收门票钱,若是不得我意,我可要找嘉靖侯退钱。”
几人小声交谈间,最前方的戏台上说书人清了清嗓子。
场中便安静下来。
说书人声音洪亮:
“话说天下分合更始,王朝此兴彼落,似为万世不易之定数,数千年来无有例外。
倘使明朝不亡于土木之役,亦难逃倾覆之结局。
有明一朝,历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十六位皇帝,享国276年。
后人言:明之亡,始于神宗。
神宗朝年号万历,始于西元1573年,终于1620年。
今儿个,我们就从神宗中期的国本之争说起。”
众人会心一笑,明若不亡,至本朝于何地?
这故事看来不是讽谏朝政的。
殷士儋道:“二百七十六年,已是有数的长寿王朝了……为何不提神宗前期,为何要用所谓西元,不知嘉靖侯有何深意。”
张居正摇摇头,继续听。
“皇后久未诞下皇子,诸大臣请立国本。”
“当时,有庶长子朱常洛可为太子。”
“前明祖训,无嫡则立长。”
“既有祖训在,如何能有争议?”
说书人停下来,喝了口茶。
有人道:“有长而不立,或因其不贤?”
二楼不少达官显贵闻言不由一笑。
殷士儋道:“或因皇长子圣质如初,有淳古之风。”
这下满堂皆笑,只有雅间内的裕王笑不出来。
说书人没再卖关子:
“只因万历帝不喜长子。
又为何不喜长子?因其母恭妃原乃慈宁宫之宫女。”
众人恍然颔首。
慈宁宫为太后居所,此间宫女诞下皇子,有伤皇帝脸面。
不想立其为太子也能理解。
皇帝也要给自己留点脸嘛。
“诸大臣以礼法为由,一再请立皇长子,神宗一再不肯,此事遂拖延日久。”
“及至1586年,宠妃郑氏诞下一子,神宗晋其为皇贵妃,其位仅次于皇后,远在恭妃之上。”
“如此,神宗之心,路人皆知。”
“户部给事中首疏反对,称‘立储自有长幼,郑妃不宜专宠’,神宗大怒,将其贬官。”
“立储一事仍争议纷纷,神宗或贬或笞亦不能止。”
众人皆颔首,看来朝中正直的清流不少。
“1591年内阁首辅申时行试图缓和矛盾,然而两面不讨好,先与群臣联名上书,后上密贴支持神宗拖延立储。
事泄,群情激愤,竞相弹劾,申时行名声扫地,被迫去职。”
此时,一人道:“嘉靖侯此事有些想当然了,内阁首辅即使名声扫地也能赖着不走呢。”
当即有人起身怒斥:“你敢诽谤严阁老?”
“岂敢岂敢,我是在说申时行,并无一言提及严字,兄台何以诬我诽谤严阁老?”
“原来如此,是在下误会了,哈哈。”竟真就偃旗息鼓。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他的成分。
于是有真严党愤而起身,狠狠环视场中,似要将笑的人全部记住。
堂内噤声不语。
说书人被打断也不恼,见恢复了安静,接着讲:
“1593年,神宗又提‘三王并封’之策欲搁置争议,群臣激烈反对,被迫收回成命。”
“1594年,被贬的京官顾宪成回乡重建东林书院,多有遭谪者往来其间,讲学议政,自称清议。”
“顾宪成刻对联于院门,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后渐演变为东林党。”
殷士儋摇头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该称东林群才是。”
大多数人点头称是,皆言若此君子之群主理朝纲,国家必不至于有倾颓之患。
“自申时行去职,接任者亦无平息争端之力,由是朝堂人心皆散。”
“神宗至1586年起,怠于政事,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十五年不上朝,至 1601年,中央和地方缺官达三分之一。”
众皆愕然,只觉滑天下之大稽,嘉靖侯果然还是太过年轻,将权力看得过于儿戏。
不过,有前面的铺垫,也能勉强算它在情理之中。
“百官各结党派,朝政逐渐败坏。”
“1601年,太后干预此事,神宗终于让步,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说书人又停下来,喝了口茶。
有人道:“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然则朝政荒废十五年,天下焉能不乱?”
“前面说明之亡始于万历,想必就是此事埋下的祸患。”
“此事虽然离奇,却并非毫无可能,嘉靖侯的想法是不错的。”
“妙啊,国本之争本是争国本,到头来却争没了国本,实在讽刺。”
张居正摇头道:“此事既是国本之争,亦是君臣之争。”
说书人接着讲:“太子虽立,此事却并未完结。”
“这十五年间,郑妃独宠于后宫,其亲族亦已成势。”
“而神宗仍留福王于京中,及至1614年方去就藩。”
众人联想起唐朝时李承乾与李泰,想必嘉靖侯的灵感来源于此。
先前又提到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太子或将反矣。
“1615年,因宫廷防卫松懈,竟有一人持枣木棍从东华门径直闯入东宫,打伤守门内官,直至前殿檐下方被擒住。”
“此事震惊朝野,群臣愤慨,皆言其必受郑妃党羽指使,意欲刺杀太子,动摇国本。”
“此人经审理供出郑贵妃贴身宦官,进而牵连郑贵妃本人,东林党遂群起指控郑贵妃谋害储君。”
台下人等议论纷纷,先前起立的严党言,此必东林党栽赃之谋。
其余人皆反对。
两派人争执不休,分外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