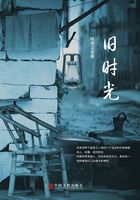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大年元宵节
元宵节相传源于汉明帝。其白天叫“上元”,夜晚为“宵”,故称“元宵”,又叫“上元节”。明帝尙佛,上元日命士庶黎民张灯敬之。至唐后,观灯便成闹元宵内容之一。历代写元宵的诗词颇多,摘撷一二以飨读者。
隋炀帝的《正月十五通衢建灯夜升南楼》,应是我国最早的元宵诗:“冰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写得既真切又可见帝心之愉悦。
李商隐写《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的遗憾:“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姜夔写灯会的意趣:“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
辛弃疾的《元夕》把元宵节通宵的热闹写到了极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元好问《京都元夕》写元宵的游乐把自己也写了进去:“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清人符曾《上元词》则专写元宵美食:“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倘把这些优美诗词仔细品,不难想见古代元宵节的繁荣阜盛和吃汤圆观花灯的热闹场景。
老家古镇把元宵节叫“大年”,似乎这年不过到正月十五就不能算完。五十年前虽说我家无糯米,汤圆吃不起,可外婆定会邀我们去乡下大快朵颐。
外婆在节前就泡好了糯米,村里家家有石磨,到推汤圆那晩你去听,除却零星爆竹响,全是“叽嘎叽嘎”推磨声。没糯米的泡上糯高粱也要“过把瘾”。元宵前夜,天空湛蓝,星儿点点,月儿浑圆,宛如银质玉盘。小媳妇穿着紫花棉衫,侧坐磨边,衣袖半挽,十指纤纤,用小木勺将雪白糯米一勺勺喂进石磨眼。大男人则甩开臂膀,转动长长“磨当根”(推磨木具),把扇石磨推得“吱溜溜”转。磨声悠扬,软语绵长,如舒伯特的小夜曲,又如高山流水般欢畅。石磨流出的糯米浆像少妇乳汁,散发奇异甜香,与四周的柴草味泥土味梅花的幽香味伴和,弥漫山野竹林,透出农历大年的温馨及古拙乡村的宁静。糯米浆推好,需倒进过滤架下的纱布兜狠摇。待水滤尽,忙将滤布扎紧,再用石磨压水分,最后将其吊于茅屋檐门。米浆袋挂檐门,乍看就像汤圆在“吊颈”。因此,在我们古镇,元宵又叫“吊颈汤圆”。很形象,亦动听。
正月十五早晨,懒觉睡醒,“吊颈汤圆”面已晾成,干湿正适应。将花生、黄豆炒熟捣均匀,加红糖、猪油等,拌成汤圆心。一人烧火众人齐包,柴火又好,火焰冲出炉灶,映红了外婆全家满脸的辛劳。很快,铁锅内比元宝还大的汤圆滚动起来,像雪球跳跃。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往上翻,跟土墙老房的昏暗对比明显。全家围着灶台喜笑欢颜,享受辛苦一年才有的幸福时间。
外婆不知从何处翻出年节方用的细瓷小碗,让各自随便舀,不够再包。说大年吃汤圆,诸事方圆满;就像这汤圆,打个滚又一年。还说,大年能吃饱,来年才有饱饭吃。——这种慷慨我家何曾有过?丢进一个烫得直吐舌,下了肚竟毫无感觉。外婆慈祥笑,言汤圆里面有铜钱,吃着能生财。而我至今未曾见,难怪到老我也与银钱无缘。表弟李世杰憨头憨脑说,来个吃汤圆比赛,看谁吃得快且多。我与四弟正求之不得,笑得喜泪婆娑。闭住双眼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横扫千军——“战绩”评定:我和四弟并列冠军。吃了多少计不准,总之是吃得天昏地暗肚儿滚圆;吃得表哥连声啧啧表弟瞠目结舌表嫂目瞪口呆;吃得四弟三天饱嗝四天酸水五天饭难下咽。他拍着孕妇般的胀肚,难受却满足,撮着小嘴悄声嘀咕:“这回饱了,饱了!”
灌饱肚皮,冒着细雨,我牵四弟与表弟一路滑溜,回古镇看热闹去。古镇三面环江,到镇必渡河。细雨朦胧间,看长河若带,水绿似玉,关山含翠,对岸笼烟。
摆渡的是三两只乌篷船,形如柳叶般,可载十人许。船舱深,两侧有木板为凳,以供坐人。船顶盖有竹篾篷,舵舱空一格,供艄公瞭望用。赶场乡民披蓑戴笠,提块“宝肋肉”,背个大公鸡——走亲戚的无疑。可惜都不是去我家的。
村姑二八许,着水印蓝花衣,把身子裹得紧紧的,显出凹凸有致。撑开红雨伞,于船头站立,纯美如深山璞玉。其余乡民亦穿戴整齐,挨挨挤挤,卷起的裤脚溅满新泥。
艄公则头缠青布棉,叼根叶子烟,神态安然,一桨一桨很悠闲。冬日水枯,平如镜,色如玉,澄清碧绿。细雨江面,漾起无数小圈。木橹过处,划出漂亮水花,荡漾开去,似灵动光环。对岸古城楼、黄葛树、老瓦屋、白沙滩,逐渐清晰,映入眼帘。
元宵的古镇笼了层雾样的雨幔,那雨飘在脸上,湿润清爽,空气浮动腊梅的暗香,吸一口,舒坦至五脏。爬上城楼望,见万头攒动,川流不息,撑伞戴笠,花花绿绿,间或可闻热闹的“晒坝子戏”,好一幅流动的古镇元宵赶集图。
爆竹钝响,十字街吼声起——是迎接踩高跷的。著戏装,画脸谱,夸张醒目。一路走一路唱,四川锣鼓格外高亢,把茶馆的、店铺的、饭馆的全引出。人集如蚁,连古色古香的木牌楼、雕花窗都被挤满。人们脖颈伸长,厚嘴大张,脑壳如木偶般乱晃。紧接是舞龙灯。四条街涌出舞龙队,腾挪跌宕,青春飞扬。舞龙人左擎红彩球,右持金项圈,时而跃起时而空翻,潇洒彪悍。看客鼓掌呐喊,声震云天。
小广场的川剧,锣鼓催人紧,踩掉鞋也难挤进。我们小孩全都噌噌上了树。滑稽戏《拜新年》,笑得我们搖树干。宿雨滑落,淋得大人缩脑壳。年节期间,大人亦有好容颜。抬眼看,细娃皆在槐树巅。除叫我们小心点,唯有摇头“干瞪眼”。不觉天晚,沿街多小吃,炒米糖,豆花饭,炸元宵,阳春面……吆喝比小吃更惹人馋。
元宵之夜,各家多爱在瓦屋檐头挂大小灯笼。石板街面被小雨洗净,一路纸糊纱灯映出人们湿漉漉的青石影,红绿赤橙,梦一般恬静。细雨渐停,玉兔东升。虽朦胧毛晕,却别有风韵,且与元宵纱灯交相辉映。天地浑然,整个古镇幻若月宫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