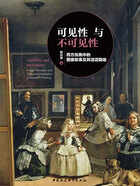
序言
如果我们自问图像转向何以现在发生,何以在人们常说的“后现代”时代即20世纪后半叶发生,我们就遭遇一个悖论。一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的是,视像和控制技术时代、电子再生产时代,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开发了视觉类像和幻象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对形象的恐惧,担心“形象的力量”最终甚至能捣毁它们的造物主和操控者的焦虑,就如形象制造本身一样古老。图像崇拜、打破偶像、艺术鉴赏以及拜物教都不是独特的“后现代”现象。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恰恰是这个悖论。图像转向的幻想,完全由形象控制的一种文化的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规模的真正的技术可能性。
——米歇尔:《图像理论》
一
图像叙事和图像观看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备受关注。在古希腊,知识被区分为“可理解的知识”和“可感觉的知识”,前者与语言文字相关,指与理性相关的知识,涉及理性的话语分析及其理解;后者与视觉图像相关,指与感性相关的知识,涉及感性的图像叙事及其观看。
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图像叙事的方式古已有之,以图释文的叙事模式在文学史和美学史上从未缺席。人类文明早期的原始彩陶、石器与玉器的造型、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原始的岩画等图像符号就承载着叙事的功能,这些符号表征着古老的神话传说或历史,记录并传播着当时的文化与生活。在古希腊时期,陶绘承担着对神话传说的叙事和解释,以及对大众的教化功能。在中世纪,图像承担着教义阐释的功能,帮助不识字的民众理解《圣经》文本。在中国,也有基于文学母题的图像叙事文本,如基于《女史箴》创作的《女史箴图》,基于《世说新语》创作的墓葬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基于《洛神赋》创作的《洛神赋图》,等等。在宋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插图画在书籍中的应用,如魏晋南北朝的《梁皇宝忏》初具连环画的雏形,文字与图像共同承担着叙事功能。
在中西美学与艺术史上,图像具有符号隐喻性和艺术想象性,本身就具有叙事功能,可以独立完成叙事。索绪尔指出,“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1]。也就是说,图像具有空间的发散性特征,能让观者在不同的接受点上感受和认知对象。图像的符号隐喻性建构了图像的叙事张力,即直观形象及其话语深度所构成的审美张力。根据索绪尔的论述,笔者认为,语言叙事是一种“不在场”的可说性符号叙事,图像叙事则是一种“在场”的可视性符号叙事。图像的“在场性”是与视觉的直接“在场感”联系在一起的。
从叙事方式来看,图像叙事具有写实性和象征性特点。图像是历史的遗留,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图像叙事直观地展示给观者实实在在的、可视可感的人像、物象和景象,再现故事发生的细节和背景。细节真实性对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图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带领观者进入故事情境中,引起观者对图像形成感性层面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更容易获得观者认同,使观者更好地体味图像叙事的表征和深层意义。此外,图像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相似,会逐渐演化为对图像符号约定俗成的共识——象征性。象征性的图像符号能够形成一种图式,获得大众的共识,形成图像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的符号指称性。
图像将人物、人物行动和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图像符号之间的组合和场景的衬托,最终完成叙事建构。图像符号作为一种直观的符号,其能指和所指的相关性决定了它在被接受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转化,它将情节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观者面前,从而避免了语言文字需要经过大脑想象和理性思维的转换才会形成叙事场景的局限。此外,通过图像描述故事情节,文本往往选取动作达到顶点前的顷刻间的现象,通过静态的画面展示动态的瞬间和暗示动作的发展,这也是莱辛所指出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2]图像的直观顷刻性被赋予深度和暗示性,当静止的绘画艺术抓住场景中最具想象性的时刻,图像无疑会因此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和想象空间。
梅洛-庞蒂认为,在绘画的图像叙事中,绘画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语言,以它自己的方式说话,这种方式依靠自然和直接的知觉器官进行表意,图像试图“和物体一样令人信服……向我们的感官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3]。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叙事是一种“不在场”的符号言说,属于可说性叙事;图像叙事则是一种“在场”的言说,属于可视性叙事。梅洛-庞蒂将图像叙事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认为图像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体叙事,因而有着“图像的肉身”的提法。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图像不同于文字的线性再现,属于非线性再现。在非线性的图像叙事中,意义呈现出空间发散性特征,使观者关注图像背后的话语表征。周宪认为,图像所营造的世界“是一种具有相对封闭性的视觉系统,图像的主题意识只能是从图像中显现,众多图像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它们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意义,或者说都可以单独表意,每一幅图像都不需要另外一幅图像的解释和说明,不再需要前后语境,图像是指向它自身,它的意义向背后延伸而不是向两边扩展”[4]。可以说,图像将客体的视觉面呈现出来,通过这种视觉再现语言或话语,会形成一种形象文本。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在同一个文本中,语言叙事与图像叙事也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中,如马格利特的绘画《形象的叛逆》,就表征了图与词的断裂叙事张力。在《形象的叛逆》中,词的否定叙事逆转了图的指称功能,词发出对图合理性叙事的否定和破坏声音。同时,图也以视觉的逼真性不断质疑词的叙事合理性,使词的叙事同样面临语言的表征危机。
在伯格眼中,观看是一门学问,它不仅是对物的观看,同时更涉及主体心理,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及隐喻的观看之道。“我们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既受到视觉对象和媒介方式的制约,同时也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自觉加工生产的过程。”[5]伯格发现,从认知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图像先于语言,如一切照片都来自连续性的断裂。伯格指出,如果图像叙事涉及公共事件,连续性便是历史;如果涉及私事,连续性便是人生;即使是单纯的风景照,连续性就是光线和气候。伯格强调,不连续性总会产生歧义,即便这种歧义不是显而易见的。[6]根据伯格的论述,图像叙事是一种不连续的断裂叙事,是对日常生活连续性的中断。为了使图像叙事合理化,就必须弥补叙事的断裂性,而这,便涉及图像叙事及其话语隐喻的分析与解读。
伯克认为,图像观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呈现,“如果认为这些艺术家——记者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也就是以为他们的眼光完全是客观的,不带任何期待,也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那也是不明智的”[7]。舒里安认为,“图画就是一种编了码的现实,犹如基因中包含有人的编码生物类别一样。……图画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8]。在舒里安看来,大自然的多样化适宜在图画里而不是话语里表达,虽然话语有可能比图画真实,但图画中包含的观点具有更丰富的色彩和内容。笔者以为,文字和图像虽然有着交融和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交往,但却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所掌握的话语权。在图像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图像所构造的并不是实物本身,而是通过符号实现话语意义的传达。图像指涉的外在自然之物与图像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们看上去相同。在图像认知中,叙事者的意图与观看者的接受在感性层面上会存在不同,即使面对图像中相同的认知点,不同的认知者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而且,话语权在观图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者对图像的阐释。
二
在西方思想史上,图像叙事与图像志、图像学、肖像学等概念有着密切关联。
图像志(Iconography)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用来描述和阐释图像等视觉艺术,由希腊语eikon(图像)和graphein(书写)衍生而来,有图像书写、图像描述和图像阐释等内涵,关注艺术品的主题与意义,如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言:“‘图像志’的后缀graphy,源于希腊文graphein,它暗示着一种纯描述性的,而且常常是资料统计式的方法。因此,图像志是对图像的描述和分类,就像人种志(ethnography)是对人类种族的描述和分类一样。……在这些研究中,图像志对我们确定作品的日期、出处,偶尔还对我们确定作品的真伪具有无可估量的帮助;它为进一步解释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不过,图像志本身并不试图作出这种解释。”[9]
图像学(Iconology)概念最早出现于里帕在1593年所写的附有插图、论及文艺复兴的《图像学》一书中。图像学一词的后缀olgy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指思想和理智,带有理性化色彩。里帕通过隐喻的方式给抽象概念下视觉定义,使人关注相关概念的全部特质,为图像解释提供参考。在里帕那里,图像学并非现代的“图像学”概念,或者说是“图像志”范畴更合适。里帕书名中的“iconologia”主要含义指古代图像及徽志的解释说明,包含了类似解释的条目。
在18世纪之后的思想史中,图像学逐渐从里帕阐释象征形象的手册,转变为研究象征形象的名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瓦尔堡(Aby Warburg)在解析占星术壁画时使用了图像学术语,随后这个概念随着瓦尔堡学派的研究进入艺术史理论的研究中。贡布里希指出,瓦尔堡的图像学与里帕的图像志不同,图像学的研究内容不是徽志和寓意画,而是形象的形式与内容在不同文化冲突中的相互作用。[10]瓦尔堡对图像志研究方法进行革新,他将艺术品主题的来源从神学式文学作品和祷告文拓宽到神话、科学、诗学、历史、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这便是图像学的雏形,因此瓦尔堡也被学界誉为“图像学之父”。在1893年以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为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瓦尔堡致力于展示15世纪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伟大艺术品的象征性,以及模仿在绘画史中的作用。瓦尔堡将图像视为通向文化深处的中介,认为图像是时代文化的征候,有着隐秘的精神象征。瓦尔堡重视图像的细节,认为图像中的隐秘文化征候并不是存在于形式或主题中,而是存在于细节中。这些细节是散布在主题之外、游离于文本边缘的符号要素,也是图像本身及其主题的附属,如维纳斯的秀发、女神们的衣饰等。
图像学(Iconology)研究的最终确立是由瓦尔堡的学生潘诺夫斯基完成的。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涉及图像的内容和形式,强调只有当图像内容的内在意义成为研究对象时,才能称为图像学。阿尔甘在评述潘诺夫斯基时指出,当图像学阐释形式时,“名字会改变,而且这种调查不会再被称为图像学,而是按照现代术语学,被称为语义学,或更准确地说是符号学”[11]。在解释图像志概念后,潘诺夫斯基强调,由于图像志的用法有着严格限制,建议重新使用较为古老的图像学概念。“凡是在不孤立地使用图像志,而是把它和某种别的方法,如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或批评论的方法结合起来以解释艺术中的难解之谜的地方,就应该复兴‘图像学’这个词。‘graphy’这个后缀表示某种描述性的东西,而‘logy’源于logos(思想或理性)——则表示某种解释性的东西。”[12]可见,图像学必须以图像志为对象来阐释内在意义。潘诺夫斯基坚持形式和风格可以阐释出内在意义或世界观,但他认为揭示世界观的阐释行为不等于图像学。图像学之名是为了配合图像志的阐释而出现的,是为了把更深层的图像志的研究区别于形式的研究才发明的。
贡布里希1949年在对莫里斯《符号、语言和行为》的评论中指出,图像学的研究工作,最终必须像语言学研究词语一样,在贡布里希看来,一般的图像学研究需要澄清莫里斯提出的形象和语言的关系。[13]在贡布里希眼中,图像关注形象的再现问题而非象征,形象实际上并不直接与它所指代的对象相关。在《木马沉思录:论艺术形式的根源》中,贡布里希认为:“图像学这个刚出现的研究学科跟艺术批评的关系就相当于语言学跟文学批评的关系。”[14]在贡布里希那里,图像学研究关注形象与语词的关系,图像学是研究形象的符号学。贡布里希在《象征的图像》中将图像志看作实证性的具体原典确定,而图像学是带有更多猜测性的研究方案重建。在此书中,贡布里希定义的图像学是一种无法确证的猜测性的图像志,图像学与图像志的边界也重新变得模糊。米歇尔笔下的图像学概念借鉴了贡布里希的理论,有趣的是,他是直接引用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而非引用《象征的图像》。米歇尔提出“批评的图像学”,希望实现对形象本性及其视觉理论的研究。
与图像学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肖像学(Iconography)。Iconography的后缀graphy源于希腊文graphein(写作),强调一种动作性,有一种描述过程或叙述一个事件的意思,带有暗示性意义。肖像学对艺术形象及其渊源展开研究,主要对艺术作品中图像的象征、题材、故事、寓意进行鉴别、描述和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肖像学是为图像学作准备的,图像学可看作一种带有解释性的肖像学。
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中将图像学研究方法描述为三个层次:前图像志分析(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研究对象为第一性或程式主题构成的母题,即通过观看即可识别的事物;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研究对象为第二性或程式主题所构成的图像背后的故事和寓意,即图像所传递出来的意义;图像志解释(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研究对象为图像隐在的内容和意义,即图像所指涉的特定主题。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学的三个层次从程式主题到特定主题,阐释内容彼此独立又相互融合,阐释范围也逐步深入。在潘诺夫斯基的理论中,图像学对内在意义与内容的解释需要追寻原典根源。根据潘诺夫斯基的理论,从图像学角度对再现性绘画展开解读,一幅再现性绘画可以梳理出三层意义来对应图像学研究的三个阶段。首先,描述画面可见之物,无须描述物与物的关系,即“前图像志描述”。其次,描述绘画“主题”,即将画面的可见之物带入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即“图像志描述”。再次,阐释艺术品深层次的意义,意味着作品中隐藏着某种观念,我们无法通过表面的视觉观看去发现这些观念,即“图像志解释”。对一个绘画的图像叙事研究往往需要以上三个阶段,但如果需要展开更深层次的阐释,需要回答“艺术家以某种方式创作一幅作品”“为什么作品的某个主题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流行”等问题,需要揭示作品主题所涉及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问题,即“图像学解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贡布里希高度评价潘诺夫斯基的研究,认为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中将图像理论学科化的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潘诺夫斯基并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但他以此为基础,发展起了一种跨学科的图像解释的规范或方法论,即图像学。[15]到了20世纪后半期,图像学的研究发生转向,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图像本身,图像学研究逐渐扩展到文学、哲学、艺术、文化等领域,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三
今天,是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也是一个读图时代。因此,对图像叙事的考察必然面对视觉文化的时代语境,挖掘读图转向视域下图像叙事背后的言说逻辑与内在机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预言:“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6]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波宣布“景观社会”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米歇尔和瑞士学者博姆提出“图像转向”命题,[17]认为语言学转向正在被一种新的转向——图像转向——所取代,即文化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18]米歇尔指出:“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另一次转变正在发生,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我想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19]米歇尔认为,图像转向使“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变”[20]。在米歇尔看来,虽然图像作为表征传达的工具自古就有,但它现在显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弗莱博格描述了19世纪开始出现的图像化景观:“各种各样的器械拓展了‘视觉的领域’,并将视觉经验变成商品。由于印刷物的广泛传播,新的报刊形式出现了;由于平版印刷术的引进,道密尔和戈兰德维尔等人的漫画开始萌芽;由于摄影术的推广,公共和家庭的证明记录方式都被改变。电报、电话和电力加速了交流和沟通,铁路和蒸汽机车改变了距离的概念,而新的视觉文化——摄影术、广告和橱窗——重塑着人们的记忆与经验。不管是‘视觉的狂热’还是‘景象的堆积’,日常生活已经被‘社会的影像增殖’改变了。”[21]可以看到,到了20世纪,图像文化日益成为社会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图像叙事逐渐取代了印刷文化时代的文字叙事,如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2]。20世纪60年代,德波用“景观社会”描述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化发展,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图像化的景观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23]。
在西方思想史上,图像转向是对语言学转向的一种承继,同时也是一种挑战,这也表明了当代哲学思想正由话语意识形态向着图像意识形态转变。在图像转向过程中,人们逐渐放弃阅读语言文字,通过语言理解文本的方式,取而代之以基于图像的视觉思维模式,传统的语言文字由于受到图像转向的影响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米歇尔认为,随着图像转向,当代体验的中心已从语言文字转变为图像,并且这一体验在维特根斯坦和罗蒂等哲学家们对于图像的恐惧与焦虑中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这种想维护‘我们的言语’而反对‘视物’的需要,正是图像转向正在发生的可靠标志”[24]。米歇尔指出,“不管图像转向是什么,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它认识到观看(看、凝视、扫视、观察实践、监督以及视觉快感)可能是与各种阅读形式(破译、解码、阐释等)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25]。米歇尔的话表明:一方面,今天的大众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视觉来体验事物和思想;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也相应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图像在当下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图像与文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关系等问题上。因此,从语言学转向到图像转向,不仅意味着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以“语言/话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向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转变。
今天,图像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特别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场中,图像俨然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角。我们生活在一种图像文化中,一个景观社会里,一个由图像和拟像所建构的世界上,图像成为最不可少的传播媒介,也使我们对于图像的熟悉度和习惯度上升至日常需求的层面,使得我们对图像文化的关注变得极为迫切,也正如贝尔所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26]艾尔雅维茨认为,图像成为时代的主角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媒介事件,更是公共空间中的一个美学事件。这正如他在《图像时代》中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在约克郡或纽约市,甚至希腊、俄罗斯或马来群岛,只要当下的晚期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地方,这‘图像社会’就都会如影随形地得到发展,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大众媒体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从二者之间建立的联系。”[27]“图像的显著优势,或曰‘图画转向’,有助于解释近年来在哲学与一般理论上的‘语言学转向’。此外,这种优势似乎也暗示出某种其他内容:词语钝化。人们常说,宗教改革不仅引起了图像的世俗化,而且也使它们在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然而,现代主义本身基本上说还是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话语。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此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化无处不在。”[28]
在图像转向思维模式下,图像文化模式取代了语言文化模式成为把握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思维模式。在图像转向的影响下,文学和媒介的发展出现了图像化趋势,图像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中心,这正如艾尔雅维茨所借用瓦侯的断言:“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29]可以说,图像转向表征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出现:图像阅读是一种后语言学或后符号学的理论呈现。米勒曾指出,新的传媒时代与读图时代的到来,必然会塑造出新的人类感受方式。旧的文学阅读将受到改变,可能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人们将被电子媒介重塑的焦虑包围。[30]从技术层面上看,多样化的技术发明连同复制技术的大规模机械生产,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视觉盛宴,也让我们对视觉性的需求更加普遍与强烈。图像摆脱传统的配角地位,转而与文字并驾齐驱,甚至占据主导性地位。各种各样的图像凭借其感性和直观性更具有诱惑力,而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所造成的种种压力也导致了现代人更倾心于视觉的狂欢与精彩。而恰恰是图像的直观性与视觉化形成了上文所言的图像霸权。现代人阅读图像更多是停留于图像的感性层面,而远非传统阅读那样上升到理性层面。与传统文学语言阅读中的读者相比,现代人更热衷于做当代图像阅读中的观者。在这个意义上,图像以其自身的禁闭世界影响观者的阅读,也阻碍了观者的深层理性思考。
视觉因素弥漫于整个社会文化空间,图像成为当下大众生活中重要的符号表征。贡布里希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在早餐读报时,看到新闻中有男人和女人的照片,从报纸上移开视线,我们又看到食物盒上的图片。邮件到了,我们开启一封封信,光滑的折叠信纸上要么是迷人的风景和日光浴中的姑娘,使我们很想去作一次假日旅游,要么是优美的男礼服,使我们禁不住想去定做一件。走出房间后,一路上的广告牌又在竭力吸引我们的眼睛,试图挑动我们去抽上一支烟、喝上一口饮料或吃上点什么的愿望。上班之后更得去对付某种图片信息,如照片、草图、插图目录、蓝图、地图或者图表。晚上在家休息时,我们坐在电视机这一新型的世界之窗前,看着赏心悦目的或毛骨悚然的画面一幅幅闪过。”[31]莱斯特也认为,在当今时代,“关注图像是人类的本能。眼睛被喻为‘心灵之窗’,人类获取信息的80%来自眼睛”[32]。正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读图时代、图像叙事、图文关系的研究在学界逐渐涌现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焦点和热点。
需要指出的是,图像增殖产生的图像多为拟像,拟像无所指涉,或者说指向虚拟现实,如奇幻电影带来的奇幻世界、广告的夸大效果、电子游戏的虚拟震惊等。种种超现实视像包围着现代人的生活,图像或者说拟像超越了现实的真实,所谓图像与客观世界的相似性原则彻底被打破,而传统意味上的艺术韵味也消融在这普遍的审美泛化之中。图像以其凶猛之势形成一股图像霸权,并在人们的认识与生活中构成一系列的断裂和重构。当下,大量的视觉符号占据了人们生活的空间,使视觉图像和形象代替语言文字符号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符号。
四
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和艺术跨媒介性是本书的重要研究视角。
在西方理论话语中,通常美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艺术哲学,如黑格尔在《美学》中开篇坦言:“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从艺术哲学的视角对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展开研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图像叙事需要从哲学层面出发,以解决“艺术何以可能”这个关键问题;其次,把艺术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以此研究艺术家的图像叙事,以及其他艺术现象,需要分析这些有关艺术哲学的具体实践是否具有合理性;再次,从艺术哲学角度探讨造型艺术中的图像叙事,对于今天的艺术批评又具有怎样的启发,这种艺术哲学思考最终能否走向一条更广泛的艺术社会学路径。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图像叙事的合理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关艺术的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分析视角,可以使我们将对图像叙事的反思建构在真实的艺术审美经验基础上。
艺术社会学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视角。艺术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艺术品总是在客观的时空中显现自身,人们对艺术品的体验、接受与认可也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基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本书不仅关注图像叙事的具体展开,也关注图像叙事中的话语隐喻,尤其是艺术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着艺术形式的生成与发展、艺术风格和流派的形成、艺术史的发展与建构,艺术材料是一种社会化的材料;另一方面,艺术同样反馈于社会,影响社会发展,特别是帮助社会个体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认知,影响个体对社会现实问题展开反思与批判。应当说,艺术社会学集结着诸如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知识和话语,它打破了这些单一学科的界限,呈现鲜明的跨学科性。艺术社会学有着鲜明的边界跨越性,先前封闭的艺术形式轻易地穿过了一度守护严密的界线,产生出与其他学科不同寻常的摩擦与关联。此外,艺术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互动,也使经典艺术学理论中的诸多核心命题焕发新的理论生机。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社会学的视角中,本书对经典艺术家的分析也尽可能保持艺术的多维阐释向度,实现美学阐释、文化阐释和社会理论阐释的相互交融。总之,通过对图像叙事的艺术社会学考察,本书试图建构一种关于艺术的复调阐释可能性,试图实现对文化形式、社会形式和艺术形式的交互性思考。
本书还秉持艺术跨媒介性的研究视角。跨媒介性是晚近学界流行的概念,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降,跨媒介性研究更是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跨媒介”这个词最早可以出现在1812年柯勒律治的使用中,1966年出现在美国艺术家希金斯的论文中。“跨媒介性”这个概念1983年由德国学者汉森-洛夫首次使用,是一个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类似的词,可以用来处理文学与绘画等视觉艺术,以及音乐等听觉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的复杂关系。媒介永远都是充满争议的领域,跨媒介更是如此。因此,跨媒介性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它总是在诸多媒介的关联阐释中而存在,是对传统单媒介接受感知形式的打破和更新。
沃尔夫认为,狭义的跨媒介关系存在于人类艺术产品的意义或影响生产中,以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辨识媒体部分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构成性关联中。[33]沃尔夫从“作品外”(extracompositional)和“作品内”(intracompositional)两个层面分析了跨媒介性,前者指不同媒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决定作品的意义和外在形态,包括超媒介性、跨媒介转换两种模态;后者则是批评家方法论的产物,并不直接影响作品的意义和外在形态,包括跨媒介指涉和多媒介性两种模态。[34]施勒特尔提出了跨媒介性的四种模态理论:综合的跨媒介性,即几种媒介融合为一个综合媒介;形式或超媒介的跨媒介性,具有超越单媒介的超媒介结构特征;转化的跨媒介性,即一种媒介通过另一种媒介来呈现;本体论跨媒介性,它是讨论任何媒介之前必须预设的某种本体论媒介,是媒介分析的根据和前提。[35]里普勒认为,跨媒介性作为一个反映媒介之间关系的关键概念,用以描述涉及范围宽泛、多种媒介参与的文化现象。这一概念涉及文学、文化、戏剧研究、艺术史、媒介等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它们均涉及不同的跨媒介问题群,需要采取特定方法和定义来处理。[36]可以看到,跨媒介性强调“跨”的特殊性,它在看到不同媒介差异性的同时,更关注媒介关系中不同媒介的交互性。
媒介是艺术存在的物质基础,艺术理论对艺术实践展开反思,必须基于媒介学视域建构自身学科。由于媒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艺术理论的知识生产和建构中,必然遭遇不同门类艺术由于差异和融合所导致的困惑。周宪认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而言,跨媒介性及其研究不但是对这一知识系统合法性的证明,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把握艺术统一性及其共性规律的独特视角。作为一个新关键词,‘跨媒介性’彰显出艺术的多样性统一以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37]。因此,通过超越单一媒介视域,研究艺术理论中带有普适性和共通性的话题,可以为艺术学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参照和关联的视角,建构艺术理论跨媒介视域的基本范式和言说立场,进而丰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复调性。
在西方艺术史上,艺术跨媒介性研究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对以诗画关系为代表的“姊妹艺术”研究中,如贺拉斯的“诗如画”命题、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命题和莱辛的“诗画异质”命题,中国古代的“诗画一律”“书画同源”等命题,始终是跨媒介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构成了跨媒介艺术研究的理论基石,这也正如卢维尔所言:诗画之间起起落落的竞争、和解与融合关系变迁,无疑是理解“姊妹艺术”研究传统的一个基本线索。[38]在西方艺术理论中,除了诗画关系外,“ekphrasis”(艺格敷词)作为一个在西方有着古老传承和历史的词,就通过探讨图与言的媒介差异性来讨论艺术间的媒介差异性。“艺格敷词”通过语言去描述图像,这其中就必然涉及不同媒介的相互关联性。在新媒介时代,技术已深度介入日常生活,也促使艺术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共同参与到跨媒介的研究当中。从知识学的生产和建构角度来看,上述研究提供了跨媒介知识生产的理论资源和话语范式。
在沃尔夫提出的四种“跨媒介性”模态中,跨媒介参照或指涉(intermedial reference)既不是媒介混杂,也不是符号的异质性构成。在跨媒介指涉中,目标媒介往往是暗含的或间接的,或者说是观念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它是主媒介所唤起的一种关于目标媒介的心理效果。沃尔夫认为,“跨媒介指涉在表面上给我们制造了媒介和符号同质的印象,但同时它却指向另一媒介。换句话说,跨媒介指涉尽管也是跨媒介性的一种形式,但它只以占支配地位的指涉‘源’的能指作为基础进行运作”[39]。在沃尔夫看来,“跨媒介指涉”中被指涉的媒介是间接的和隐蔽的。拉耶夫斯基在分析跨媒介性的亚类型时,也提出“跨媒介指涉”概念,认为这是一种“通过使用自身特定媒体手段,主题化、唤起或模仿另一种传统上截然不同的媒介元素或结构”的跨媒介形式。[40]根据沃尔夫和拉耶夫斯基的观点,笔者以为,在传统的美学研究中,媒介只是一个美学思辨的载体,而“跨媒介性”概念的提出,将注意力放在具体的媒介及其表征方式上,这就将经验分析与思辨研究结合起来,能更合理地阐释艺术及其表征观念的交互性张力。以此来看,本书所讨论的诸多绘画作品,其实也是一种跨媒介的主题指涉,即绘画作为一种主媒介和一种符号系统,它通过符号隐喻指涉隐藏其后的语言或话语,呈现图与词、图与言的跨媒介关系。
海索拉斯认为,媒介总是相对于其他媒介而存在的,跨媒介性作为本体论的必要条件,总是出现在“纯粹”和特定的媒介之前。因此,媒介必然是从初始的跨媒介性中提取出来的。[41]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艺术媒介的阐释复杂性,就必须围绕跨媒介性展开更具总体性的跨问题域考察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对绘画艺术展开图像叙事的隐喻分析,以此进入更宽泛的跨艺术研究、美学视域下的艺术类型研究和艺术史的语图关系和图文关系研究,我们都看到了跨媒介视域的影子,它包括比较文学、艺术学、美学、文学、媒介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的洞见,这也在客观上提醒我们:跨媒介视域的艺术研究,本身也理应是多学科、多媒介的融合,需要跨学科的阐释视域。
语言与绘画的关系是无限的,彼此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如果绘画可以指向一个语言文本或与之相联系的思想观念,我们就涉及语图关系的跨媒介性研究。如果我们认为,在绘画中,画面其实指涉的并非画面本身,而是画外之音,那么我们实际上已遭遇了两种媒介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这也正如委拉斯凯兹、马奈和马格利特的作品以及福柯的解读所表明的那样:画面媒介指涉语言媒介,试图对传统画面表征所体现的理所当然的再现或理性话语进行质疑和颠覆。在本书所分析的诸多作品中,被指涉的话语媒介只是作为一种观念隐藏在作为主媒介的画面中,而并非一种实体的媒介存在。由此,我们便涉及更宏大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层面的跨媒介话语范式建构,即基于艺术史和文化实践,将不同媒介及其关系和张力置于相对宏观和系统化的艺术史和社会文化体制中展开分析和探讨。基于此,以绘画为主媒体,可以探讨绘画艺术中图像与语言的复杂关系和叙事隐喻。这是一种跨媒介叙事学的讨论,实现了对绘画的图像叙事和语言叙事的张力关系考察,提供了从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视觉艺术等复调层面展开跨媒介艺术的叙事研究的理论可能性。剖析这些作品,进而结合艺术史发展的具体情境,为解读跨媒介叙事中的复杂图文张力提供新的思考路径。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绘画作为一个表征媒介,它是如何呈现被表征的媒介,以及不同媒介之间形成了什么样的话语联系或张力。
本书引入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和艺术跨媒介性视角,侧重于从社会理论、美学、文化、哲学和艺术等若干视角相融合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展开探讨,意在考察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是如何介入艺术学的问题域,同时也意在勾勒艺术学话语是如何向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渗透的。
五
本书选择艺术史上的经典个案,剖析其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以期对当下的图像研究话题进行回应。通过对西方绘画艺术的个案剖析,本书试图挖掘画面图像的视觉机制及其叙事建构,进而结合艺术史展开叙事话语隐喻的深度思考,如诗学隐喻、文化隐喻、意识形态隐喻等。
本书关注三个关键词:图像表征、叙事建构、话语隐喻。在这三个关键词中,“图像表征”是艺术现象层面的考察,也是本书的个案支撑。“叙事建构”是图像表征的深层学理剖析。“话语隐喻”研究图像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呈现出图像学研究的独特言说立场,是进一步的深层学理研究。在总体思路上,本书舍弃现象描述与价值表态的研究模式,试图从个案与学理相结合的层面展开讨论和思考,一方面为当下的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为解读当下的艺术理论提供实践支撑。
本书立足于问题意识,以艺术史上的代表性艺术家和经典艺术现象为线索进行章节建构。本书每一章聚焦一个艺术家或一种艺术现象,以此探讨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第一章讨论古希腊陶绘的图像叙事建构。本章以神话传说母题的陶绘图像化为切入点,探讨图像叙事对神话传说母题的语义转化及其背后的复杂张力。第二章讨论中世纪绘画的图像叙事建构。中世纪的图像,尤其是手抄本插图,并非为我们提供理解世界的透明形象,而是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某种象征意义。本章还集中讨论了反图像崇拜现象,在中世纪的反图像崇拜运动中,视觉图像成为一种禁忌,图像以象征符号的方式存在,强调图像背后的宗教教义传达。第三章讨论艾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的图像叙事建构。本章基于潘诺夫斯基的理论,从图像学的视角解读艾克作品背后的象征意义和话语隐喻。第四章到第六章基于委拉斯凯兹、马奈和马格利特的绘画创作,对他们作品中的图像叙事建构展开思考。在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图》、马奈的《弗里-贝尔杰酒吧》和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中,传统绘画的再现原则遭遇困境,图像不再成为再现的载体,出现了“再现危机”。第七章基于福柯的视域,对图像叙事的“再现危机”展开考古学分析。在古典绘画中,图像是现实世界的视觉形象再现,通过可视性的再现符号,提供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形象。福柯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对委拉斯凯兹、马奈和马格利特的作品展开分析,阐释了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型中的再现危机。基于福柯的视域,结合艺术史发展的具体情境,我们不仅看到福柯意欲建构图像叙事中的再现知识学谱系,同时也看到图像叙事背后潜隐的复杂话语深渊,同时也为我们反思现代艺术如何通过再现重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塞尚作品中的图像叙事建构以及梅洛-庞蒂的解读。塞尚在绘画中强调自然的真实视觉经验建构,他放弃了传统的绘画技法和主题,希望在风景和静物画中回归物性的自然本身。塞尚扭曲透视,拒绝把事物重叠和复制出来,而是试图呈现事物被我们所凝视的方式,显现事物的真实和深度,展现出现代艺术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梅洛-庞蒂认为,塞尚面对的挑战是传统的古典主义绘画和印象派绘画,塞尚的绘画践行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原初知觉经验的观看。第十章以绘画作品中的镜子意象为研究对象,对镜像的图像叙事及其背后的话语隐喻展开思考。本章试图梳理绘画史上镜像符号的再现特征:符号与相似性的确证(能指对所指的确证);符号与相似性的偏离(能指对所指的偏离);符号与相似性的断裂(能指对所指的断裂)。笔者以为,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再现原则,现代主义更关注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技法。现代艺术不再强调逼真地再现现实,日益转向艺术的再现方式,实现了从“艺术再现什么”到“艺术如何再现”再到“艺术拒绝再现”的转型。
本书不想建构以史带论的艺术分析模式,而是注重以论带史和以论证史,试图实现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相交融的学术话语建构。本书力图以问题意识来还原和建构艺术史上图像叙事的走向及其话语隐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展开对图像叙事的基本格局、研究范式和言说立场的思考。本书既有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艺术学理论分析和现象解读,也有哲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和文化理论的泛学科思考。笔者以为,对这些话题的讨论以及围绕这些话题的对话和争论,可以超越专业化、学院化的理论“樊笼”,彰显当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复调性和跨界性。
[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6页。
[2]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3]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忠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68页。
[4] 周宪:《审美话语的现代表意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5] [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6] [英]约翰·伯格、[瑞士]让·摩尔:《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7]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8] [德]瓦尔特·舒里安:《作为经验的艺术》,罗悌伦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9]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志和图像学》,[英]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附录。
[10] [英]E.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55页。
[11] Argan,G.C.,“Ideology and Iconology”,Critical Inquiry,1975,Vol.2,No.2,p.303.
[12]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志和图像学》,[英]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附录。
[13] Gombrich,E.H.,“Review”,The Art Bulletin,1949,Vol.31,No.1,pp.72-73.
[14] [英]E.H.贡布里希:《木马沉思录:艺术理论文集》,曾四凯等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15] [英]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编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页。
[16]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
[17] 米歇尔用的概念是“the pictorial turn”,博姆用的概念是“ikonische Wendung”。在米歇尔看来,图像转向是由皮尔斯所研究的非语言的象征系统的符号学,逐渐转变为由视觉艺术充斥着的符号系统。米歇尔还认为,图像转向也体现在古德曼对“艺术语言”的描述中;现象学对想象的关注中;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语言中心论”的批判和对“延异”概念的阐释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与反思中;福柯话语的和视觉的事物的断裂的分析中,等等。而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则将“与现代/后现代”的区分与“话语/图像”区分联系起来,认为即现代以理性的、话语中心的语言学模式为主导,而后现代则以呈现为感性的、图像中心的视觉模式为主导。
[18] 最先提出“视觉转向”(visual turn)的是美国艺术史家莫克西,他的文章《视觉研究和图像转向》发表于2008年第2期的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文章首次提出视觉文化概念,区分了两种视觉文化研究方法。一种是源于文化研究的方法,以米尔佐夫为代表,探讨在社会的语境中形象的文化和政治功能,注重对象的意义或意识形态编码,属于符号学和权力话语分析;另外一种是图像转向的方法,以米歇尔、埃尔金斯、波姆、布雷坎普和贝尔廷等为代表,注重对象的在场、物理地位和生命品质,具有本体论的视角。在莫克西看来,文化研究式的视觉文化把对象看作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而图像转向式的视觉文化把对象看作呈现(presentation)。
[19] [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3页。
[20] [美]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哗译,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1] [美]安妮·弗莱博格:《移动和虚拟的现代性凝视:流浪汉、流浪女》,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328页。
[2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23]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4] [美]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哗译,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5] [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6]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页。
[27]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8]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9] [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在书中,艾尔雅维茨借用了瓦侯的这句断言作为章节的标题,以此来说明图像时代的到来。
[30]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1] [英]E.H.贡布里希:《贡布里希论设计》,范景中选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32] [美]保罗·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霍文利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3] Wolf,W.,The Musicalization of Fiction: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Intermediality,Rodopi:Amsterdam and Atlanta,1999,p.37.
[34] [德]维尔纳·沃尔夫:《文学与音乐:对跨媒介领地的一个测绘》,裴亚莉等译,《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
[35] Schröter,J.,“Four Models of Intermediality”,Herzogenrath,B.,Travels in Intermediality:Reblurring the Boundaries,Hanover:Datmouth College Press,2012,p.5.
[36] Rippl,G.,“Introduction”,Handbook of Intermediality,Berlin:DeGruyter,2015,p.1.
[37] 周宪:《艺术跨媒介性与艺术统一性: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方法论》,《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
[38] Louvel,L.,The Pictorial Third:An Essay into Intermedial Criticism,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18,p.1.
[39] [德]维尔纳·沃尔夫:《文学与音乐:对跨媒介领地的一个测绘》,裴亚莉等译,《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
[40] Rajewsky,I.O.,“Intermediality,Intertextuality,and Remediation:A Literary Perspective on Intermediality”,Intermédialitéi,2005,No.6,p.53.
[41] Herzogenrath,B.,Travels in Intermediality:Reblurring the Boundaries,Hanover:Datmouth College Press,2012,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