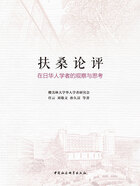
三 长期萧条的微观原因之二:政府失灵与过度管制的延续
(一)干预经济及保护既得利益的政策偏向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介入,在早期着重于开发与振兴,官僚处于指导者的地位。由于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明确,且处于高速增长的时代,政府的干预较少出现阻碍民间经济活力的偏差。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政府的作用更侧重于协调和再分配。这时维护产业秩序,限制竞争的倾向越来越突出。
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决策系统是典型的条块分割型官僚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31]在制定微观经济政策时,部门或业界立法的特点较为突出。其立法过程是,首先由各主管部门内部开展调查、通过审议会等研讨进而拟定草案,再交由相关部委调整、折中,并进一步形成内阁提案,经执政党党内审查后提交国会审议并表决。在政策形成的实际过程中,主管部门的官僚往往代替大臣调整或斡旋,相关利益团体主导了审议方向,而族群议员左右着党内审查。这里,业界团体协会与主管部局,以及获得各业界支持的政治家议员(俗称族议员)构成了牢固的“铁三角”。由此,在现存利益集团(产业团体协会等)的压力下,日本的微观经济政策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既得利益集团优先、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优先的政策偏向。
在金融方面,直到20世纪 80年代末期政府都对银行以护送舰队方式加以保护:政府制定各种限制竞争规则,支持银行通过卡特尔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以帮助银行消除破产的风险。由于不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竞争,银行缺乏创新能力,经营模式僵化,业务单一,竞争力下降。同时由于长期的保护,银行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政府心理,道德风险问题比较突出。在80年代后期大企业出现远离银行的倾向时,银行大量无节制地贷款给房地产,直接助长了泡沫经济。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又疏于检查和督导,不仅不督促银行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反而在一段时期里要求银行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救助。如政府在90年代后期明确要求银行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核要求,在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重组时政府还明确要求接手企业必须答应继续保留长期信用银行的小企业贷款支援业务。可以说政府的压力也是各金融机构加大对衰退产业或僵尸型企业贷款的原因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重新恢复了对衰退企业的保护和救助,在当年11月发表了对中小企业贷款放松条件的方案,放宽了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2009年11月民主党政权还制定了中小企业金融圆滑化法案,进一步对中小企业贷款条件以及银行中小企业债权的分类大幅度放宽标准,从法案制定到2011年6月,相当于GDP7%左右的巨额资金在优惠条件下贷给了相关企业。这项法案两次延长,到2013年3月才结束,也可见保护措施一旦出台便往往难以撤销。[32]
在实体经济方面,各业界的利益团体除工会外均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紧密联系。特别是农业、建筑、邮政、医疗、交通运输等大团体作为自民党的“大票田”,对自民党政权的决策影响甚大,所以政府历来对这些产业实施严格的准入管制,加以层层保护。最典型的例子,是70年代初国家为了保证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米价,并在此后为了防止农民种植过多而导致米价下跌,实施了对所有农户一律调整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反”及补贴政策。此举背离了1961年制定的农业构造基本法,其结果是保护了零碎农业种植户,挫伤了规模经营专业户的积极性。[33]在其他许多受到产业政策保护的领域里,也出现了竞争力下降的问题,竹内弘高等对9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成功的20种产业和失败的7种产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成功产业大多没有产业政策支持,失败产业则多是产业政策管束过多、特别是限制竞争较多的部门。[34]此外在区域间资源配置方面,从70年代田中角荣政权时代开始,政府为了消除所谓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现象,对特大城市(京滨及阪神工业地区)经济活动加以各种限制,如限制工厂设置,减少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投资,对劳动力的自发流动给予管控等;与此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幅度增加了对地方经济的资金扶植,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地方公共事业,人口稀少地区也纷纷上马建设工业园区。凡此种种干预,均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下降。[35]
此外,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整个1990年代,历届政府多次推出了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公共建设事业。[36]不动产建设部门在泡沫经济中负债过多,本应在90年代受到压缩,但多次公共大投资延缓了这些产业的调整和重组。许多财政投资继续投向收益低甚至是无效益的地方,既浪费了资源,又导致了财政赤字及累计债务的大幅度上升。这种做法直到2001年小泉任首相后才开始有所缓解。
总之,政府对传统产业的过保护,以及对新兴企业准入或竞争的种种限制,直接弱化了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能力。而且由于族群政治家、主管官僚与业界的关系过于紧密,寻租行为长期存在。在立法或制定政策过程中,企业或财团向政治家、官员行贿的事件屡见不鲜,直到数年前,官员“下凡”到大企业里担任高管的现象还十分普遍。
(二)政策调整机制失灵与放松管制改革的停滞
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日本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1993年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体制崩溃,形成了多党联合体制及其后的自民党与公民党联合政府。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也开始加速,如1994年将选举制度改为小选区加比例代表制,1995年的政党补助法及1998年中央部委改革法的出台等,一系列的改革都对原有的政治格局及政策形成机制冲击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导致各业界利益诉求增加,而民众特别是消费者权益意识也大大增强,加之全球化竞争及外国政府的政治及经济的压力等,使得影响政策的因素增加,决策过程复杂,政策难以出台。原有的铁三角调整机制已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而新型调整机制无法有效确立,加之政权流动性极大,导致泡沫经济以后多项微观经济政策改革滞后,或问题久拖不决。这也是日本经济新陈代谢能力下降的原因。
比如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这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快速反应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政府不作为的典型。不良债权问题久拖不决,首先,与政府特别是当时的主管部局的大藏省对银行的监控和检查失灵,对不良债权额判断错误,以及银行系统依赖政府决策有很大关系。其次,特别是在处理不良债权的第一轮过程中,由于对非银行的住宅专门金融公司的救灾优先照顾了农协金融的利益,且财政埋单,导致法案出台后遭到国民强烈的反对。此后政府与政治家对不良债权的问题采取了回避和拖延的态度。最后,大藏省官僚的晋升制度及银行经营者的晋升制度都导致主要官僚及银行行长不愿在本人任期内暴露或深究不良债权问题,而绝大多数政治家,包括1997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也对问题的严峻性没有清醒认识。这些原因致使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时机大大拖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金融机构的问题总爆发,导致了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直至小泉担任首相后的2002年,在政府的严厉督促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才开始得到严格处理(村松,2005;奥野等,2007)。[37]
再比如从90年代起,尽管各届政府均提出要大力放松管制,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以及政权的不稳定,许多改革设想迟迟难以得到推行,传统的旧制度依然具有极大的惯性作用。江藤分析认为,日本政府从90年代起虽然放松了经济类管制,但同时却强化了社会类管制,如住宅、土地、公共设施建设类,基准和资格认证类,环境、安全、资格类,法律、保安类,以及医疗、幼儿保育、教育等类别。[38]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自我评价,在放松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方面,2005年电信、金融、公路运输、制造、零售行业的管制水平只有过去的二、三成,但受社会类管制较多的工业废水废弃物处理行业、医疗、教育、社会福祉等公共服务业的平均管制程度反而上升了10%—30%。[39]
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经过巨大努力而决定实施的改革在政权更迭后也出现了倒退。小泉政权时代制定的几项放松管制或民营化改革方案,比如2002年放开出租车市场、每年司法考试增加三千名法律各类人才、放开派遣员工管制制度等改革,特别是邮政民营化改革也在其辞职后几年之内被修正或重新加以管制。改革倒退的原因在于业界团体以及政治家势力的卷土重来。业界团体提出了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出租车市场放宽准入将增加事故”、“司法考试增加录取人数将降低法律人才的素质”、“派遣制度加剧了劳动力之间的待遇差距”、“邮政事业民营化及邮政四大领域的分割会降低邮政服务的水平”等。[40]
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等原因,后小泉时代日本在放松管制上雷声大雨点小。Haidar(2012)对世界银行公布的172个国家从2006年到2010年间开展的放松管制改革数量加以统计,发现各国平均改革数量为6.5项,而日本同期只有3项。他还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各国放松管制数量与其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如果日本达到平均改革水平的话,GDP增长率可提高0.525%。[41]
放松管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日本的营商环境魅力不足。如世界银行对2011年的183个国家与地区开展商业活动的难易度排名,日本总评虽然居第20位,但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在具体的10个项目管制程度的排名中,设立有限公司开业一项由于非常费时、费成本而排在第107位(OECD国平均申请时间为12天,日本为23天;必要手续OECD平均5个,日本为8个),税收手续及负担率项目排在第120位(日本企业税率平均为49.1%,纳税所花费时间为330小时,远高于OECD平均186小时)。其他突出的问题还有建筑开工许可手续审查严格、时间过长,不动产登记手续繁杂等(表3)。[42]而在OECD 2012年发布的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管制程度的排名中,日本的管制状况在OECD成员国中最为苛刻,总指数高达0.265,远超过OECD甚至全部调查对象56国的平均值(图9)。[43]
表3 2011年世界各国(地区)企业活动容易程度排名


图9 海外直接投资限制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OECD(2012)制作。

图10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及吸引外资余额(10亿日元)
资料来源:根据“财务省本邦资产负债余额”制作。
上述数据均表明日本的管制制度过于严格,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开展商务活动。企业全球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调查发现,2012年日本创业活动比率只有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7%,与周边的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相比较也低很多,在统计的68国(地区)中处于末位。此外日本新企业的开业率不到3%,开业率和废业率均远低于美英等国,说明企业的新陈代谢的确较慢。[44]在投资方面,尽管小泉上台后就力推吸引外资,但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依然严重不足,最近几年因金融危机影响外资直接投资余额还有所减少,相反日本企业大举向海外转移(图10)。以上所列举的创业难、吸引外资难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政府管制过严且改革滞后作为主要原因难辞其咎。其结果是不仅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也如前文所述,导致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流出而新兴企业或外资企业难以进入的问题,阻碍了产业和企业的新陈代谢,降低了TFP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