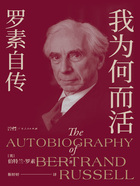
1872年—1914年
第一章 童年,少年
多亏大自然、书籍,以及 数学的拯救,才让我免于彻底的沉沦
我最早的清晰记忆,是我在1876年2月来到彭布罗克庄园1时的情景。准确来说,我并不记得到达这里的确切情形,只是零星记得途经一处伦敦火车站,那大概是帕丁顿站,有着巨大的玻璃屋顶,在我看来简直美得不可思议。我对到达彭布罗克庄园第一天的记忆,就是在佣人休息室里喝茶。这是一间陈设简陋的大房间,摆着一张大长桌、几把椅子和一把高脚凳。所有的佣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喝茶,除了女管家、厨子、贴身女仆和男管家之外,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贵族圈”,在女管家休息室里自成一统。我被人放在那把高脚凳上,最历历在目的回忆,是当时纳闷这些佣人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大法官、几位赫赫有名的女王御用大律师和各路知名人士紧密关注的对象。直到长大成人,我才了解来到彭布罗克庄园之前发生的奇事。
我的父亲是安伯雷子爵,长期以来,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并于不久前去世。大约在之前一年半,我的母亲和姐姐死于白喉。后来,我通过母亲的日记和信件了解到,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活泼、机智、严谨、独创和无畏之人。从照片来看,她生前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则冷静达观、勤奋好学、脱俗、孤僻且自恃清高。两人都是激进的改革理论家,一心要把自己坚信的所有理论付诸实践。我的父亲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的学生和好友,在他的影响下,我的双亲倡导节育和妇女选举权。我的父亲因提倡节育而丢掉了议会中的席位,我的母亲也偶尔会因激进的观点而遇到麻烦。在玛丽王后3的父母举行的一次花园招待会上,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呵斥:“没错,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罗素家的儿媳。但现在我却听说,你只爱和龌龊的激进派和肮脏的美国人为伍,传得整个伦敦满城风雨,所有的俱乐部都在讨论这件事。我真要看看你的衬裙,是不是也一样脏。”
我母亲生前常常在会议上发表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演讲,我在她的日记中找到了一段话,将包括西德尼·韦伯夫人4和考特尼夫人5在内的波特姐妹称为“交际花”。日后,我与西德尼·韦伯夫人日渐熟识,相比于母亲,她的确较为轻浮,这也让我对母亲的庄重肃然起敬。然而,从我母亲的信可以看出,她有时也会展现风情万种的活泼一面,比如,她在写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6的信中就是如此。这么说来,她展现给世人的一面,或许并不像日记中表现得那么让人畏惧。
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名为《宗教信仰分析》7的大部头著作,在他死后出版。他有一家巨大的图书馆,里面有教父学、佛教、儒学论述等著作。为了创作的准备工作,他在乡下待了很长时间。我的父母在院长院子8有一幢房子,在婚后最初几年,他们每年都会在伦敦待上几个月。
1867年,我的父母去了美国,与波士顿激进派广交好友。他们无法预见到,那些充满民主激情、博得他们掌声的人,那些成功反对奴隶制、引得他们钦佩的人,却正是日后那些谋杀萨科和万泽蒂9的刽子手的祖辈。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二十二岁。就如哥哥在自传10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他在父母婚礼后九个月零四天时降生。在我出生前不久,一家人搬进了一所僻静的宅邸,名叫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现名克莱登庄园)11,坐落于威河陡峭堤岸的树林中。我出生三天后,母亲在家中给她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我:“婴儿体重 磅,身长21英寸,又胖又丑,大家都认为很像弗兰克。蓝色的眼睛分得很开,下巴轮廓不明显。他对母乳哺育的态度和弗兰克一模一样。我现在奶水很足,但如果他没能立即吃上奶,或是遇到诸如胀气等情况,就会恼羞成怒,大喊大叫,胡踢乱颤,直到有人安抚才停下……他会高高抬起头,充满活力地环顾四周。”
磅,身长21英寸,又胖又丑,大家都认为很像弗兰克。蓝色的眼睛分得很开,下巴轮廓不明显。他对母乳哺育的态度和弗兰克一模一样。我现在奶水很足,但如果他没能立即吃上奶,或是遇到诸如胀气等情况,就会恼羞成怒,大喊大叫,胡踢乱颤,直到有人安抚才停下……他会高高抬起头,充满活力地环顾四周。”
父母为我哥哥找来的家庭教师名叫道格拉斯·斯伯丁12,詹姆斯13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对他的论述做了援引,这至少是对其科学素养的一种证明。他是达尔文主义者,热心钻研鸡的本能,为了便于研究,他获准把家中包括起居室的每个房间都折腾得一团乱。当时,他本人已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离世了。显然,我的父母基于纯粹的理论作出决定,鉴于他身患结核病,理应不生子女,但因此要求他独身则有失公允。因此,母亲便允许他跟自己同居,但据我所知,她并未从中获得任何乐趣。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始于我出生之后,而母亲在我两岁时便去世了。然而,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却让这位家庭教师继续任教。父亲去世后,人们才得知他安排这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14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这样安排,是希望保护两个儿子免受宗教教育之害。然而,我的爷爷奶奶从父亲的信中发现了关于我母亲的事情,使得秉承维多利亚道德观15的两人惶恐不安。他们决定在必要时启动法律程序,从蛊惑人心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两位心怀不轨的异教徒找到霍勒斯·戴维16爵士(后为戴维勋爵)咨询,爵士确信两人赢不了官司,显然是基于雪莱17的先例。因此,我和哥哥便判为法院监护,科布登-桑德森在上文提到的那天将我交给了我的爷爷奶奶。毫无疑问,这段历史加剧了佣人们对我的兴趣。
关于母亲,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一次我从小马拉的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她肯定在场。我对这段记忆多年闭口不提,很久以后找人得到了证实,因此,这段回忆很可能是确切发生过的。关于父亲,我只有两段回忆:我记得他给了我一页红色的纸,颜色我很喜欢;另外还有一段他泡澡的场景。我的父母选择葬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花园中,后来被挖出迁到了切尼斯的家族墓室。
爷爷奶奶居住的彭布罗克庄园,是里士满公园里的一幢形状不规则的老旧别墅,只有两层高。乔治三世18对彭布罗克夫人19情有独钟,在爆发精神错乱的那一年,将这座别墅作为君王的赠礼送给了她。20女王在爷爷奶奶四十多岁的时候把别墅赠予他们,从那之后,他们便一直住在那里。彭布罗克庄园有十一英亩的园林,其中大部分区域的植被都可自由生长。在我十八岁以前,这座园林是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园林的西侧,从埃普索姆丘陵(小时候的我还以为这片丘陵叫“上上下下丘陵”21)一直延伸到温莎城堡,中间则是欣德黑德和利斯两座山丘。我逐渐习惯了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一览无余的落日,从那以后,若是少了这两种景象,我的生活便少了许多乐趣。那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栎树、山毛榉、欧洲七叶树、西班牙栗树、欧椴树以及一株非常壮美的雪松,还有印度亲王赠送的柳杉和喜马拉雅雪松。那里有凉亭、锈红蔷薇灌木丛、月桂树丛和各种各样的藏身处,即便成年人躲在这里,也完全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另外,园里还有几处欧洲黄杨围成的花圃。在我入住彭布罗克庄园的这些年里,园林越来越疏于照管。大树倾倒,小径上灌木丛生,草坪上的野草长得又高又密,那些黄杨树篱几乎长成了大树。这座花园似乎还留存着对于昔日辉煌岁月的记忆,那时,异国的使节在草坪上踱步,亲王们观赏着修剪整齐的花坛。这片园林活在往昔,而我则和它一起流连于往昔。我编织着有关父母和姐姐的旧梦,想象着爷爷尚且身强力壮的日子。我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大多讲的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爷爷在厄尔巴岛拜谒拿破仑22,奶奶的叔祖如何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捍卫直布罗陀,以及她的祖父因为埃特纳火山的山脊上有充足的熔岩,主张世界一定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之前23,并由此遭到政府排挤。有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会转向较为近期的时事,他们会告诉我卡莱尔24如何称赫伯特·斯宾塞25为“纯粹的真空”,或者达尔文如何因格莱斯顿先生26的来访而倍感荣幸。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我常常好奇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常在园林中踱来踱去,时而捡拾鸟蛋,时而冥思时光的飞逝。如果可以依据自己的回忆做评判,那些对性格塑造影响重大的孩提印象,尽是些全神贯注于童稚之事且不能对大人倾吐的短暂瞬间。在我看来,不受外界强加之事的打扰而随心所欲探索浏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时期,才能让人有时间形成那些看似一晃而过,实则灵动鲜活的印象。
记忆中的爷爷已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浴椅中被人推着在园中散心,就是坐在他的房里阅读《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27。爷爷去世时,我刚刚六岁。记得在他去世的当天,我看到哥哥(他当时离家上学)坐着马车回家,但当时还在学期期间。我欢呼了一句:“万岁!”但我的保姆却制止我说:“嘘!你今天绝对不能说‘万岁’!”从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推断,爷爷在我心里的分量并不太大。
相反,比爷爷年轻二十三岁的奶奶,却是我整个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名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属自由主义者(她在七十岁时成为一位论派28信徒),但对于一切道德问题都极其严苛。嫁给爷爷的时候,奶奶还是个羞涩的少女。爷爷是个鳏夫,膝下有两个孩子和四个继子女。两人结婚几年后,爷爷便当上了首相。对她来说,这想必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她说,还是个姑娘时,她曾参加过诗人罗杰斯29举办的一场著名的早餐会。看到奶奶的羞涩,罗杰斯对她打趣道:“亲爱的,吃点口条吧,说不定能让你健谈些!”从她的言语中可以明显听出,她根本不知恋爱是什么滋味。有一次,她告诉我,在蜜月期间,母亲过来陪她,让她如释重负。还有一次,她哀叹道,如爱情这般无足轻重之物,竟能成为如此多的诗歌的主题。但对于爷爷,她堪称一位忠诚的妻子,而且据我所知,她向来将为妻的严格标准奉为己任,从未有过疏忽。
作为一位母亲和祖母,她虽关怀备至,但并非时时明智。我觉得,她从不知晓动物本能和旺盛生命力的需求,而是要求通过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滤镜审视一切。记得我曾试图让她明白,一方面要求每个人有住处安身,另一方面又因为新房子碍眼而反对建造,这未免自相矛盾。在她看来,每一种感情都有各自的权利,不能仅因符合逻辑这种冷冰冰的东西就给另一种感情让位。按照她那个时代的标准,她是位教养良好的妇女:她能够准确无误地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且丝毫没有口音;她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和18世纪的诗人如数家珍;她能背诵黄道十二星座和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根据辉格党的传统,她对英国历史了解得细致入微,也熟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典作品。自1830年以来,她对政治有了近距离的亲身体悟。然而,在她所受的教育和她的精神生活中,却从未涉及何谓理性。尽管我已听过不知多少人试图向她解释,但她就是不明白河上船闸的运作原理。她恪守着维多利亚清教徒的道德观,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一个不时口出脏话的人也能拥有些许优良的品质。然而在这一点上,也偶有例外。她认识贝里姐妹30,她们是霍勒斯·沃波尔31的好友。一次,她丝毫不加谴责地对我说:“她们有些守旧,只是偶尔说几句粗话而已。”像她这样的人,大多会在谈及拜伦32时网开一面,觉得拜伦因年少时爱而不得饱受折磨。然而,她对雪莱却没有这样的宽容,她认为雪莱的生活毫无道德可言,也觉得他的诗歌无病呻吟、令人生厌。我觉得,她应该从未听说过济慈。虽然她通晓直到歌德和席勒的欧洲大陆古典文学,但对她同时代的欧洲大陆作家却一无所知。屠格涅夫曾经送给奶奶一本他的小说,但她从未读过,只把他当作某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友。她知道他在写作,但觉得几乎所有人都能动动笔杆,因此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她也同样一无所知。她认为,某些动机是值得称赞的:比如对国家的爱、为公精神、对孩童的爱。然而,对金钱和权力的爱以及虚荣心,则皆为不好的动机。好人的行为总是出于善的动机,然而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并非时时邪恶。婚姻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制度。显然,丈夫和妻子有义务彼此相爱,但又不应太轻易地履行这一义务,因为如果两人是因性吸引力而结合,那么便一定有什么不体面之处。当然,她并不会用这样的措辞来表述这个问题。她曾经说过:“你知道吗,我从不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像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那样纯洁,因为这种感觉偶尔会掺杂些自私的意味。”言语之间,其实就是在暗指这个问题。这或许是她所能想到的最接近性爱这个话题的表述了。隐约记得有一次,我听到她在谈及这个禁忌话题时稍进了一步:当时,她谈到帕麦斯顿子爵33在男人中作风不正,因为他不是个检点的人。她不喜欢喝酒,憎恶烟草,饮食习惯近乎素食主义。她生活简单朴素,只吃最清淡的食物,总在八点钟吃早饭,在八十岁之前,从未有过在饮茶后坐在舒适座椅上休息的习惯。她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看不起那些看重世俗荣誉的人。恐怕,奶奶对待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也不很恭敬。她曾经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在温莎城堡,她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女王和蔼地关照她说:“罗素夫人请坐吧,某某夫人,请站在罗素夫人前面。”
在我十四岁以后,我开始对奶奶在见识上的局限心生厌恶,她那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觉得过了头;但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对我的用心良苦以及对我的幸福快乐的关怀备至,让我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赋予了我作为孩子所需的安全感。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想如果奶奶有一天不在人世,那该有多么可怕。而她真正过世是在我结婚之后,我却全然没有感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越发意识到她在塑造我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畏,她的为公精神,她对传统的蔑视,她对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无视,向来是我认为值得称道也值得效仿的品质。她给了我一本《圣经》,扉页上写着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一条是:“不可随众行恶。”34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让我在日后的人生中从不畏惧成为少数派中的一员。
除了奶奶,我的家中还住着我的叔叔罗洛和姑姑阿加莎,两人当时都没有结婚。罗洛叔叔在我的幼年成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他对科学问题颇有见解,也经常与我讨论。叔叔曾在外交部任职,但他眼睛有疾,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无法读写。后来,他的视力有所好转,但却再也没有尝试过任何常规工作。他是一名气象学家,对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研究,那次火山喷发给英国带来了落日奇观,甚至出现了蓝月亮。他时常跟我讲起落日奇观由喀拉喀托火山导致的证据,我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谈话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
在饮食方面,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受到极其严苛的管制,饮食之清淡,远远超过了当今人们视为有益于健康的程度。里士满住着一位名为德切戈扬夫人的法国老太太,她是塔列朗35的侄女,经常送我大盒美味甘醇的巧克力。一周七天,我都得把巧克力四处分发给大人吃,而我只有在星期天才能获准吃上一颗。记得有一次午餐时,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换了盘子,且每个人都拿到了一颗橙子。大人不让我吃橙子,因为当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觉得水果对孩子有害。我知道我不能主动要求,因为这么做很失礼,但等到佣人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盘子的时候,我便鼓起勇气开口说:“这盘子里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但还是没人给我橙子吃。我吃不到水果,几乎不能吃糖,连碳水化合物也不能多吃。尽管如此,除了十一岁时轻微发过一次麻疹之外,我从来没生过一次病。自从自己的孩子出世后,我对孩子产生了兴趣,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我小时候那么健康的孩子。但我敢肯定,无论哪位现代儿童饮食方面的专家,都会认为我理应患上各种营养匮乏引起的疾病。也许是偷沙果的习惯救了我一命,如果这事在当时被大人发现,一定会引发巨大的恐慌。
童年大部分的岁月里,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光都是我在园中独自度过的,而孤独也成了我人生中最鲜明的色调。我很少向别人提及自己比较严肃深沉的想法,偶尔提及,也会心生悔意。我熟悉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年复一年,我都会到同一个地方寻找白色报春花,在另一个地方寻找红尾鸲的巢,在盘根错节的常春藤中寻找金合欢绽放的花蕾。我知道在哪里能寻找到最早盛开的蓝铃花,也知道哪棵栎树的树叶最早发芽。记得在1878年,一棵栎树在4月14日就发出了嫩芽。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两棵黑杨,每棵树大约有一百英尺高,夕阳西下时,我常能看到房子的影子悄悄爬上树。我早晨起床很早,有时能看到金星升起的情景。有一次,我错把金星看成了林中的一盏提灯。大多数的早晨,我都会迎接日出,在晴朗的四月天,我有时会在早餐前溜出家门长途漫步。我目送夕阳将大地映成红色,将云朵染成金色;我倾听风吟,为电闪雷鸣而心潮澎湃。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孤独感变得越发强烈,也越发为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心之人而绝望。多亏大自然、书籍,以及(日后)数学的拯救,才让我免于彻底的沉沦。
然而,我童年的最初几年还是快乐的,直到青春期来临,孤独才变得令人窒息。我有两位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女家教,我挺喜欢她们,且我的智识还没有充分发展,因此尚能忍受家人在这方面的不足。然而,我一定隐约感到了某种不快,因为我记得自己曾多么希望父母都还在世。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向奶奶表达了这种感情,而她却告诉我,他们的死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当时,她的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还以为是嫉妒心使然。我当然不知道,从维多利亚式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有着充分的依据。奶奶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虽然她在这大千世界历尽千帆,却从没有学会隐藏情绪的艺术。我注意到,只要稍微提及精神错乱,她就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于是对原因做了诸多猜测。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有个儿子在精神病院。他曾在一个严苛的军团参军,几年之后就疯了。
十一岁时,我开始研读欧几里得36,哥哥做我的辅导老师。这是我人生中一桩恢宏的事业,如同初恋一般炫目。我从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在我学会第五公设37之后,哥哥告诉我,这是一条公认难懂的公设,但我学起来却毫不费力。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还是有些脑力的。从那一刻起,直到我在三十八岁时与怀特海完成《数学原理》为止,数学向来是我的一大爱好,也是我快乐的主要来源。然而,与所有的快乐一样,这种快乐并不纯粹。我受的教育告诉我,欧几里得的确做出了证明,但得知这些证明是从公理推出的,我感到非常失望。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哥哥不能拿出某种理由证明这种推理方法,我就拒绝接受得出的公设,但哥哥却说:“你要是不接受这些公理,我们就没法往下讲了。”我希望继续往下学,因此只得暂时接受。当时这种对于数学前提的质疑一直伴随着我,也决定了我后来研究的方向。
刚开始接触时,我觉得代数要比几何难得多,问题或许出在教学方法上。老师要求我死记硬背:“两数的和的平方,等于两数平方之和加上乘积的两倍。”我完全搞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在我背不下来的时候,老师就把书往我脑袋上扔,这对我的理解力丝毫起不到刺激作用。然而,一旦度过了入门阶段,余下的学习便顺利起来。小的时候,我喜欢靠显摆知识让新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十三岁那年,我家新来了一位家教,我转起一枚硬币,家教问我:“硬币为什么会转?”我回答说:“因为我的手指形成了一个力偶。”他问:“你对力偶了解多少?”“嗨,没有我不了解的。”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奶奶总是担心我太过用功,因此把我的课时安排得很短。结果,我便常常在卧室里偷偷点上蜡烛学习,在寒冷的夜晚,我会穿好睡衣坐在书桌前,只要听到最轻微的响动,我就立马吹灭蜡烛,钻回到床上。我讨厌拉丁语和希腊语,觉得学一门没人使用的语言纯属荒诞。我最喜欢数学,其次是历史。由于没有其他人比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和其他男孩相比是好是坏。但记得有一次,我听到罗洛叔叔在前门跟贝利奥尔学院38院长乔伊特39告别时说:“是的,他的表现的确挺优秀。”不知为何,我一听就知道他谈论的是我的功课。一旦意识到自己脑袋灵光,我就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在知识领域有一番作为。整个青年时代,我从不允许任何事情阻碍我实现这个抱负。
若说我的童年尽是严肃认真,则完全是一种曲解。我尽情地从生活中发掘乐趣,其中一些乐趣恐怕要落入恶作剧的范畴。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留着羊排形络腮胡的苏格兰老者,他常常坐着一辆四轮马车来,在病人讲述病情时,马车就在大门外候着。他的马车夫戴着一顶精致的大礼帽,意在宣传他的医术高明。我常会爬上屋顶,把腐烂的玫瑰花蕊从屋顶的排水沟捞出来,扔到大礼帽的帽顶。随着一声悦耳的“啪唧”,花蕊在帽顶上四处飞溅,而我则迅速缩回头,让车夫以为花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年都会和罗洛叔叔一起住上三个月,他有三头奶牛和一头驴子。驴子比奶牛聪明,学会了用鼻子打开田间的栅栏门,但是据说,这头驴子不但不守规矩,而且根本没法骑。我偏不信邪,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我学会了不用马鞍和缰绳骑驴。驴子又踢又跳,但除了我在它尾巴上系了一罐咔嗒作响的石子那次,它从没有把我甩下来过。那时,我常常骑着驴子漫步乡间,甚至去找沃尔斯利子爵40的女儿玩,要知道,她家离我叔叔家有大约三英里的距离呢。
总的来说,我的童年单纯而快乐,我对接触到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抱有好感。记得我成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41时,一个明显的变化开始出现。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喜欢使用俚语,装出一副漠然的样子,还往往拿“男子气概”的一面示人。我开始瞧不起我的家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极端避讳,且荒谬地认为爬树危险。我事事处处受人限制,这也让我养成了骗人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二十一岁。出于习惯,我会认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是讳莫如深为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由此产生的隐瞒事实的冲动。每当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时,我仍想把正在读的东西藏起来,至于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做过什么事,我一般都会避而不谈。这种冲动是多年来在各种荒诞禁令中摸索前行的结果,只有凭借一定的意志力才能得以克服。
我的青春期充斥着孤独和不快。无论在情感或智力领域,我都不得不对家人守口如瓶,而这也让他们颇为匪夷所思。当时,我的兴趣投入在性、宗教和数学三个领域。回忆青春期对于性的痴迷,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虽然不愿重温那些年的感受,但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复述事实,而不加以主观的粉饰。关于性知识的启蒙,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名叫欧内斯特·洛根的男孩跟我提到的,他跟我在幼儿园曾是同学。一天晚上,我俩同睡在一个房间,他跟我解释了交配的概念以及对于生育的作用,还列举了几个有趣的故事。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现生理反应,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当时的婚姻与基督教的迷信有着紧密的关联,但在我看来,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我很肯定,这种认知是在我第一次得知性知识后不久便产生的)。我十四岁时,家庭教师说我不久后就会经历生理上的重大变化。那时,我已经多少能明白他的意思了。
几个月后,提醒我青春期即将到来的那位家教说,男人的胸部叫胸膛,而女人的胸部叫乳房。这句话让我血脉贲张、一脸震惊,而他则挖苦我大惊小怪。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求一睹女人身体的欲望中度过,我也曾趁女仆换衣服的时候透过窗户偷窥,但却次次都没有成功。我和一个朋友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挖了一间带一条狭长地道的地下室,得手脚并用才能爬进去,地道的另一头,是一个六立方英尺的空间。我常会引诱一位女佣陪我下到地下室中,在这里亲吻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肯去死,而我也信以为真。另外,她也表达了自己的讶异,说她本以为我是正经人。就这样,这段情事无疾而终。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摒弃了青春期前对性爱的理性主义观点,全盘认可并接受了传统视角。我开始变得病态,觉得自己心术不正。与此同时,我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细致而理智的研究。但我却被告知一切内省都属病态,因此,我把对自己思想和感情的兴趣视为心理失常的另一层证据。然而在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却恍然意识到,既然自省是大量获取重要知识的唯一途径,就不应被谴责为病态。这种领悟,让我在自省的问题上如释重负。
伴随着生理上对于性的痴迷,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也随之产生,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结的根源在于性。我对日落、云彩和春秋的树木之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是一种对于性的无意识升华,即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因此蒙上了一层多愁善感的特质。我广泛地阅读诗歌,从《悼念》42这样拙劣的诗歌开始读起。记得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便读完了弥尔顿的所有诗作、拜伦和丁尼生的大部分诗作,还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最后,我接触到了雪莱的诗作。遇到雪莱的作品,纯属机缘巧合。一天,我在莫德姑妈丹佛街住处的客厅里等她。我打开雪莱的诗集,恰好翻到《阿拉斯特》一首。在我看来,那是我读过的最美的诗篇。当然,引起我如此爱慕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首诗的虚无缥缈。我刚读到一半,姑妈就回来了,因此我只得把诗集放回书架。我问大人是否认为雪莱是位伟大的诗人,却发现他们对他评价颇低。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他的喜爱,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他的作品,而且熟记于心。由于找不到人倾诉自己的所感所思,我常常心想,如果能认识雪莱该有多好,同时也怀疑到底能不能在世间遇到一个如此与我心有戚戚的对象。
我从十五岁时开始相信,生命及物质的运动,都要完全遵从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对实体不能产生影响。在这个阶段,我习惯把自己的想法用希腊字母记录在一本《希腊文练习册》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生怕别人发现我的心中所想。在这本册子里,我记录了人体是一台机器的理念。成为唯物主义者的进程,本应给我的大脑带来满足,但出于几乎与笛卡尔43(当时的我只知道他是坐标系的发明者而已)一模一样的理由,我却得出结论,认为意识是不可否认的“材料”44,因此纯粹的唯物主义并不存在。那是我十五岁时的想法。大约两年之后,我开始相信死后没有生命,却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因”45的论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十八岁那年,在入学剑桥前不久,我阅读了《约翰·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父亲告诉他,“谁创造了我?”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因为这个问题马上就会推导出“谁创造了上帝?”这个问题。而这句话,也让我放弃了“第一因”的论点,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在长期质疑宗教的过程中,我因渐失信仰而心情低落。没想到在这段时间终于画上句号时,我却为放弃宗教而欢欣鼓舞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饱览群书。自学的意大利语,已经足以用来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利46的作品。我读过孔德47的书,但对此人的评价并不高。我读过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逻辑体系》,并细心做了摘要。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卡莱尔的作品,却完全否认他对于宗教纯粹感性的论证。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如果某个神学命题不具有科学命题所需的论据,就不该被接受。我还阅读了吉本48的作品,米尔曼49的《基督教史》和未删节的《格列佛游记》50,书中对于犽猢的描述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我开始通过这个视角来审视人类。
在此必须说明,当时,我的所有这些心理活动都被深深隐藏了起来,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不露任何痕迹。在社交方面,我害羞、幼稚、笨拙、安分守己、和颜悦色。看着那些在社交应酬上不知尴尬是何物的人,我心中不无歆羡。有一个叫卡特莫尔的年轻人,我猜他的品行八成有些不端,但我却看到他和一个年轻亮眼的女子走在一起,举止轻松而亲昵,显然很讨她欢心。我认定,自己必然、肯定、绝对一辈子也学不会取悦让我倾心的女性。
就在十六岁生日的前夕,我被送到伦敦老绍斯盖特的一所陆军补习学校,那个区域当时还是乡下。我之所以被送到那里,并非为了参加陆军考试备考,而是预备参加剑桥三一学院51的奖学金考试。然而,除了一两个“离经叛道”之人要当神职人员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准备参军的。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是十七到十九岁的小伙,因此我在那里年龄最小。他们会围坐在一起,讲些淫秽下流的故事,并抓住一切机会讲污言秽语。
尽管我之前也偷偷关注性爱,但如此粗鄙露骨的方式还是让我深感震惊。我开始转向一种非常清教徒式的理念,认为不以深厚感情为基础的性是极其粗俗的。
我很快就意识到,要想逃避他们的注意,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都坦然自若、和颜悦色。过了一两个学期,又有一个惹人揶揄的男孩来到补习学校,但与我相比,他是个一点就着的人。这样一来,大家也就放过了我。另外,我也渐渐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大惊小怪了。然而,我依然郁郁寡欢。有一条穿过田野通往新绍斯盖特的小径,我常常一个人去那里看日落,默想如何了结自己的生命。然而我并没有自杀,因为我仍然渴望继续探索数学。当然,如果家人知道这种内容的谈话竟会在补习学校大行其道,一定会吓得够呛,但由于数学成绩不错,我大体还是希望能够留下来,因此对家人只字不提学校的风气问题。在补习学校待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大的奖学金。去剑桥上大学前的十个月,我一直住在家里,补习学校雇了一位家教来给我做辅导。
在这段时间,我与家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在政治上仍然意见一致,但在其他方面却毫无共同点。起初,我有时还会试着跟他们聊一聊我在思考的问题,但换来的却总是嘲讽,我也因此变得沉默寡言。在我看来,人类的幸福显然应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但却惊奇地发现有些人竟然不以为然。我发现,人们会给对于幸福的信仰冠以功利主义之名,并将之简单视为某种平淡无奇的伦理理论。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仍然坚持信奉自己的观点,甚至不假思索地向奶奶承认我就是个功利主义者。她对我百般嘲讽,从此之后便老是提出些伦理学上的难题,让我依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我感觉到,她并不具备反对功利主义的正当理由,她的驳斥在智识上也站不住脚。在发现我对形而上学产生兴趣时,奶奶告诉我,整个形而上学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什么是心?心非物。什么是物?物非心。”这句话重复了十五六遍后,我就不再觉得好笑了,但奶奶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态度,却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
记得在我成人之后,有一次,奶奶对我说:“听说你又在写书了。”那种口吻就好像是在斥责:“听说你又有一个私生子了!”她对于数学虽然并不极力反对,但却很难相信这门学科能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我的冀望,是能成为一名“一位论”的牧师。二十一岁以前,我一直对自己的宗教观点守口如瓶。我发现在十四岁以后,如果想捏着鼻子在家继续待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我的兴趣全然缄口不提。奶奶谈吐诙谐,虽然表面幽默,但实则充满了火药味。当时的我还不知该如何反唇相讥,只是暗自受伤和难过。我的姑姑阿加莎也一样恶毒,而罗洛叔叔正沉浸在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悲恸之中,变得阴郁孤僻。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哥哥已经皈依佛教,他告诉我,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包裹在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起了见过的所有最小巧的信封,想象着灵魂如心脏一样透过信封跳动。从与哥哥的谈话中,我得以一窥佛教的神秘莫测,却没能从中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后,我们俩便很少相见,家里人都认为他心术不正,因此他也很少和家人打交道。我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但却从不期待遇到一个能交朋友的人或是能够倾吐心声的对象,更不敢奢求能在一生的任何阶段摆脱这种忧悒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