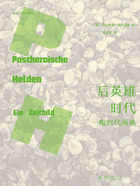
导言 英雄与后英雄:对立共存
一篇关于英雄,也包括后英雄之英雄的社会学文章,需要自陈其意义所在。如果这篇文章是为诊疗时代症候(Gegenwartsdiagnostisch)而作的,就更应如此。我们通常会把英雄与勇武好斗,甚至带有悲剧性的人物联系起来,他们做出超越常人的举动,对抗强大的敌人,抵御灾难,在逆境之中砥砺突破,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置自身于危难之中;他们漠视规矩和老套的繁文缛节,并因此受到尊敬和钦佩。一份包含上述内容的文献,与其说是社会学的时代图卷,倒不如说是浪漫故事、军事檄文、教谕文学或大众神话的图卷——社会学处理起英雄化的问题来终归不易。因为它感兴趣的是小人物,而非伟人;更注意频率分布,而非奇点;它关注社会秩序,而非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男英雄或女英雄是否必须存在?对此必要性的疑虑丝毫不亚于对英雄生成机制本身的质疑。社会学将英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怀疑,将其归为那个前现代的、等级僵化的世界里无可救药的过时遗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对理解当下帮助都有限。
面对时代症候,不仅要找到正确的答案,更要提出正确的问题。毋庸置疑,为了描述当代社会,比起考察英雄形象的危机和变迁,有更好的研究路径。就算是对英雄特质的问题化处理也不一定总能达到批判的效果:我们常常打着去魅的旗号,却在无形中继续着英雄所表征的那个等级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每当‘英雄’备受推崇时,我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英雄以及为什么需要英雄”1 1 这一评注应一并引申至社会学研究中来。这一问题意识同样可以被用来质问当下,即“我们生活在后英雄时代”这一命题。这一时代诊断容易助长一种错觉,即一种令人满意的、扁平化的后现代社会不需要英雄,也无须创造英雄。概因后英雄社会视个体之“伟大”为谵妄,要以谈判沟通来解决矛盾冲突,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志愿牺牲的行为。因此,在后英雄时代,我们同样需要问:谁需要英雄,以及为什么需要?
不管是英雄叙述还是其后英雄转向都充斥着政治渗透,我们有必要对其意图和效用质问,与此同时,也可以借此来获得解锁当下的力量:这些英雄和后英雄叙事可被视作范例,展现社会制度对其成员的期待,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取信于人,它以哪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情感机制来约束人们,它准许或褫夺什么样的主体性,又让哪些想象成为可能。此外,本书还探讨规范化的愿景和层级制度,评估一致性和差异性、主体诉求和公共诉求、个人在高度复杂的机械化运转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领导范式、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由之而来的面对死亡的态度问题,也评估性别角色或宗教纽带的重要性。谁需要英雄人物,为什么需要;谁又否定这种需求,为什么否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对危机的认识和对常规化的期许。
上述话题充满争议,所以截至目前,人们尚未就英雄主义的价值定位达成共识。笔者接下来的思考,其出发点来自一个充满矛盾的观察:一方面,自1980年代以来,“后英雄”这一定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大量出现,人们宣称其能够被用来进行时代诊疗;另一方面,也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男性或女性英雄被召唤出来,或者是经典的英雄剧目被再次搬上前台。唱衰和鼓吹英雄气概的声音并驾齐驱。随着传统的“英雄阵地”逐渐褪色,此前从未出现过英雄的领域里繁衍出了全新的英雄。英雄主义叙事的号召力可能减退了,但其娱乐价值似乎并未被动摇。那些现实中我们不忍再见的被缚的榜样,被我们在想象的世界里更加狂热地追寻。
有关未来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科学论述首先察觉并指出了后英雄时代的来临。据其论点,西方社会不再能够动员大规模的牺牲,也不再能接受自己的军队遭受长时间的巨额损失。这促使他们利用高科技武器系统发动不对称战争,然而,敌手会以殊不畏死的英雄气概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这就使得他们更易受到伤害。与此同时,组织和管理理论家们公布了后英雄的领导范式。这些范式告别了计划型政府的乐观主义,也告别了理性管理的“操纵幻觉”,转而青睐一种参与式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旨在提升人们自我控制的潜能,或主张在自我面临的实际选择中,以后英雄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再是英雄式的。心理学研究则鉴定出了后英雄人格在当代的社会特征,它通过不断适应加速前进的社会变革而获得灵活性。据说,连流行音乐都迈进了“不反文化的反文化主义”2 2的后英雄主义阶段。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中的佐证可以补充进来。即便形形色色的讨论枝节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脱节,彼此之间并无密切关联,它们仍然共同凝结成了时代的画卷。
“后英雄”几乎只作为形容词被使用,这一点令人震惊。后英雄可能会在所有领域被提及,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后英雄者或后英雄主义的讨论。与其他带有“后”这一前缀的时代标记一样,这一定语也无法用精确的概念来阐明。有时,它指一种精神气质或举止特征;有时,它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作战形式。“后英雄”也可用来定义一种对治理艺术(Foucault)的理解,这种艺术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因此抛弃了技术官僚主义治国的傲慢。此外,这一定语也用于描述某些态度和情绪,它们对激情程式(Pathosformel)过敏,对牺牲的呼吁无动于衷,或者拒绝接受毫无保留的身份认同,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伟人及其事迹崇拜持挖苦讽刺态度。最后,与这类心态相关的物件和文化实践(Kutuelle Praktiken)也被描述为后英雄。
正如谈论后现代并不等同于告别现代一样,标记后英雄时代的意向并不意味着英雄主义导向的终结,而是使其具有了问题性和反身性。将当下诊断为后英雄时代,意味着在语意上指涉那些英雄叙述的断裂并与之划分界限。但是英雄主义号召的凝聚力和动员力绝未枯竭。后英雄主义社会一方面认为英雄形象值得怀疑且已经过时,可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着从未间断过的对英雄的饥渴。这种渴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漫画和电脑游戏的世界中满是被重塑和被全新创作出的英雄,超级英雄大片实时打破票房纪录,竞技体育中英雄人才辈出。“9·11”事件中的消防员被称为英雄,气候活动家、吹哨人和政治自由斗士们同样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英雄主义不再与职责和效忠联系在一起,新英雄更被刻画出反成规和拒绝顺从的特征。英雄气概表现为勇于表达自我、刚正不阿。英雄气概成了公民勇气。与此同时,被指称为英雄的对象经历了民主化和日常化。最终,就像大卫·鲍伊(David Bowie)承诺过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哪怕只有一天”,抑或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言,在大众传媒时代,每个人都能拥有哪怕只有“十五分钟的名气”。3
然而,随着民粹主义领袖的崛起,另一种英雄类型卷土重来:他不是一个体现法律权威的父亲形象,而是反法律权威的带头大哥,因为对其人而言,法律不够专断独行。他唤起一个暴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力量最重要,只有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能获得机会。他任由追随者们宣泄情绪,而不去关注社会的繁荣稳定。他告诉追随者们对哪些人冷酷残暴可以不受惩处。他将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区别置之一旁,唯强调其个人的权力意志 3 :谁对事实核查不屑一顾,谁就可以肆意捏造事实。这些“民间英雄”进行个人表演,商业巨擘、意见领袖和军阀首脑间相互攀比,挑衅般地展示他们拥有的惊人私产,他们的外表不仅要亮丽炫目,还要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摆出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姿态,向女性发出唯有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是真正的权势人物的讯号,但又绝不仅限于此。无政府主义者也很难将他们推翻下台。他们叫嚣着,满嘴英雄主义伴随着暴力威胁和对弱者的鄙夷,与胸怀坦荡、具有大无畏勇气的平民英雄们(Alltagsheldinnen)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同英雄模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英雄与后英雄范式之间的碰撞,勾勒出当代社会的裂隙与冲突。在本篇中,我将探究这些共时的对立面 (diesen gegenstrebigen Gleichzeitigkeiten),动态考察当代英雄化与去英雄化之间的话语前沿(die diskursiven Fronten)和混合区域。我将讨论英雄叙事(及相应的消费)中情感(affektiv)、道德感、合法性和号召性的面向 ,并关注对这些面向具体的相对化处理(Relativierung),批判和消解。因此,我既不附和“我们生活在后英雄社会”这一论断,也不排斥它。相反,我对针对时代症候而作的二阶诊断 4 感兴趣。二阶诊断考察那些谈论我们当下的言说。一方面,在许多不同领域,当下被认为具有后英雄的特征。另一方面,英雄的生产在我们所处的当下仍然在全速运转。在这一背景下,有哪些当代特征被聚焦,又有哪些被边缘化了?当代英雄主义回应哪些挑战?“后英雄”这一定语回答的又是哪些问题呢?
风评认为,在诊疗时代症候的过程中,人们易将个别突出事例泛化至普遍情况,有时只依据个人道听途说的轶事作出判断,以致其结论戏剧化地前后矛盾,它忽视新旧事物之间的延续性,优先考虑贴标签,而不重视分析差异。这些论断被认为“有趣,但也有一点不可靠”4。对后英雄社会的诊断,将在这里得到批判性的阐释。虽然其本根植于当代诊断之中,但也只是作为一种平行的行动而存在,即这样的诊断或多或少仍然在粗略地使用着同样的标签,这些标签被用来描述迥异的当代现象,它们的效力面和解释力都是不确定的。
为避免社会学研究容易宽泛的陷井,我在对英雄的社会形象以及英雄主义的驱动力和影响力进行分析考量时嵌入对时代症候的探求(第一章)。它并不等同于一种英雄主义理论(那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由异质模块汇聚构成的启发性方法,引导我们深入英雄主义理论的核心层面。接下来的部分涉及英雄崇拜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与其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我追溯了从黑格尔(Hegel)到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之间的范式,进行了反思,同时揭示了后英雄主义对“英雄主义的现代性”5的摒弃。通过对阐述后英雄人格的社会心理学篇章进行话语分析(第三章),对后英雄主义管理(第四章)、后英雄主义战争(第五章)和对那些为后英雄主义社会所承认或是在后英雄社会中产生的男女英雄们的类型学(第六章)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将研究视野从思想史移开,并聚焦在当下。材料选择方面,除了科学论文和新闻素材,我还利用指南类文献(通常指成功学、心灵鸡汤类书籍)和其他流行文化现象,察明英雄人物形象在当下如何以后英雄之名被进行去中心化改造。它将他们发配至不易引起他人警觉的领域,用庸碌的日常生活圈禁其非凡之处,或者将他们置于待机状态——危机一旦发生,他们便随时可被激活。在后英雄时代,英雄的形象充满矛盾,其首要特征即在于他能够灵活地在“开机”和“关机”这两种模式间来回切换。
英雄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我们无法对它无动于衷。英雄形象以情动的方式蔓延开去。我对此深感疑虑:有太多的情绪,太多的阳刚之气,太多的道德指摘,太多的自我克制,太多的死者崇拜。在结语部分,我尝试让反英雄主义的情动贯穿全书,我将继续利用它们展开一场激进的质问。在这里,倘若我宽泛地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一本书名,提出要对英雄主义进行“否思”, 65 那就最好不要抱有一种廉价期望,认为在摆脱对英雄的渴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英雄相思病”这回事上可以一劳永逸。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巨大幻梦。只要政治或宗教制度仍依赖于献身精神,只要被普世化了的竞争仍在驱动人们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并驱使他们参与其中;只要充满无助感的经验仍在滋生关于伟大的幻觉,而日常规范仍煽动着人们对僭越的渴望——人们就会一直寻觅并找到英雄。英雄是一种标志,他们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必然想到是那里出了问题。他们又是一种索引,指向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即便英雄主义本身及其外在表现看起来与此截然相反,英雄仍然更多地表现为危机出现,而非危机解除的征兆。7
对英雄主义的“否思”并不仅限于对其后英雄转义的描摹。相反,它始于拒绝,拒绝将假定的所谓虚假与真实英雄气概进行二元对立区分,而不对后者进行审问。需要讨论的并非英雄行为本身,而是那些支撑英雄主义的框架:毫无疑问,那些挺身而出与强者抗衡,或者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自愿置身于险境之中的人令人尊重、值得钦佩。然而,宣称一些人是英雄,并要求他人效仿这些榜样,就将道德情状变成了规范说教 6 。任何借助英雄榜样的力量来说服他人,要求后者做出壮举、牺牲的人,都将英雄用作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反之,英雄们被推至遥不可及的位置,以致其行为似乎从源头上就无法被复制,这巩固了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一些人抬头仰望,而另一些人被他人仰望;一些人的职责就是领导,而另一些人寄望于被领导。英雄模范超义务地承担着履行着自己的分外职责,他们也许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但不得不提的是,他们主要通过让人良心不安来达到这一效果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英雄主义的“否思”意味着把英雄化理解为一种号召手段,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受到诱导,抑或有意识地诱导自己做出壮举,承认等级制度,把社会看作一场持续的斗争,并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将自身幸福旁置。这种号召的效能也源自英雄主义叙事的魔力。正是感人至深、激动人心的传闻故事,促动我们将男女英雄们捧上神坛,我们想要效仿他们,或者沐浴在他们的荣光之中。因此,对英雄主义的“否思”总意味着讲述不同的故事,或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
1 译文引自[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原文为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哲学教师吉瓦那·博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于2001年12月对哈贝马斯进行访谈的记录。全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在哲学领域,文化主义本身与人类学相关,强调文化背景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些支派,如方法论文化主义,指科学研究和理论形成,要以对既往文化成果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的系统性梳理和考察为基础。但文化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复杂问题,如有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左派,因受文化主义思想影响,已经演变成纯粹的文化左派,他们不再呼吁废除特权,不再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有意忽视阶级对立问题,转而捍卫起城市自由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这表明他们在实践中忽视了文化主义的“历史哲学使命”。时至今日,其特点变成了拜金、泛道德化,大搞夸张的身份政治等。基于此,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主义开始强调,相较于其他社会因素,文化对个人产生的影响被高估了。文化主义的对立面,亦即此处提到的反文化主义,有观点认为其对应于自然主义,但应当指出,除文化外,社会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在发挥着影响力,反文化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并不能简单画等号。而即便文化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文化本身无错,“不反文化的反文化主义”即基于此背景而来。
3 “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理论中的关键词。尼采认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唯意志论”(Voluntarismus)中涉及的意志,只是生存和生殖等较低层面的生活意志,而高级的、具有追求性的意志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论把追求权力、要求统治一切事物、征服所有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的意志看作宇宙的本原。
4 此处移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的二阶观察(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概念,二阶诊断即指对诊断者及其诊断结论的再诊断(观察、评估等)。例如,通过分析一阶诊断如何得出结论的过程,查找其盲点,观察出其先验与潜在结构,从而发现诊断者的局限性,得到反身性的认识。
5 否思(kaputtdenken),译名引自郑莱:《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读书》, 1998年第5期;[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按照郑莱的说法,沃勒斯坦对19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的挑战,矛头所向是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社会科学取向。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乃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种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社会……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转换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转而追问“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
译者在此特别提示,“否思”是理解本书作者意图与方法的关键之一。沃勒斯坦的“否思”可被视作对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一文中提出的该如何看待“理想”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回应。举“国家”这一实例,沃勒斯坦试图解决的不仅是理论问题、现实问题,更有方法论问题。对事物进行否思,意味着要将其原有的概念认知打破,从源头和底层重新出发。“否思”是一种破坏性思考,其方向、路径与反思,或再思不同,并因此具有更彻底的颠覆性。
6 在平面美术、制图的透视法中,依据人们的视觉经验,凡是平行的直线都消失于无穷远处的同一个点,即消失点(Fluchtpun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