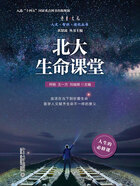
导言:生如夏花,死若秋叶
柯 杨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是泰戈尔《飞鸟集》中最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应该也是迄今对生死最美好的比喻与想象。古往今来,生与死,是人类永恒思考的话题。老子说,死生为昼夜;李白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古罗马塞涅卡说,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死亡就已经开始;日本村上春树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法国蒙田说,生之本质在于死,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英国塞缪尔说,疾病通常是一个等式的开始,完成这个等式的则是死亡……
然而,普罗大众如我们每个人,面对死亡却难有哲人诗人们的坦然与通达。因为惧怕,从古人的炼丹修仙,到现代科学的基因改造,人类从未放弃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努力。曾经,宁波灵峰寺有一座葛仙殿,传说是享年81岁、人称“小仙翁”的东晋人葛洪隐居炼丹之地。他在《抱朴子·内篇》的《金丹》和《黄白》篇中,总结了前人的炼丹成就,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描述了古代炼丹的历史脉络。古代有成千上万想通过此道实现长生不老的人,这个案例只是一个缩影。炼丹者的失败结局自不必提,而现代基因改造还真貌似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事实却是,那些改造了基因、生存期明显延长的低等实验动物的生存状态往往是低代谢、低活力,浑浑噩噩、萎靡不振。换言之,生命之延长是以降低生存质量为代价的。它违背了有性繁殖中生命进化的既定“法则”——靠新生命提供新选择,结局是物种的优化(适应)和保存繁衍。这个自然大法恐怕难以破解。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人类通过有性繁殖策略繁衍,意味着可以更高效地产出不完全一样(多样性)的后代,为一直变化的复杂生存环境提供可被优选的“样本”,使人类在适应中更好地生存,更好地繁衍。代价则是完成了生殖任务的个体自然衰老、淘汰。死亡成为有性繁殖的物种基因里“加刻”的密码,这无疑是对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和追求“自由意志”、靠聪明大脑而非肌肉雄踞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的嘲弄。面对必然的死亡,我们似乎只能感到恐惧与无奈。
我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粗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少年时,心底突然有一种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随年龄增长有所消减。第二时段是学医毕业后的很长时间,尤其是深度参与医学院校的管理工作之后。我虽然没从事临床工作,但在医院环境中目睹了各类病患的死亡过程。多年来我们的临床现实是:各种终末期的病人往往忍受着疾病和治疗带来的双重痛苦,去面对濒死感受的绝望、恐惧与无助。多数人由于对终末期毫无了解和预先准备,只是被动地接受必要和不必要并往往带来附加痛苦的各种治疗,甚至没有被陪伴和平静告别的机会,更谈不上尊严。而家属也束手无策地承受着巨大的焦虑和悲痛。多数情况下,医务人员由于理念和已形成的医疗模式等问题,除了针对疾病的治疗(如果不是过度治疗),对患者生命的终结,或不知自己有帮助患者“善终”的义务,或不知该如何施以援手。
对临终患者的这种态度是医学“失温”的集中、极端体现。医学从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出于苦难的同情与帮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汇集了人类智慧,发展了技术、变成了学问、转变成职业,最终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专门机构和社会建制。在这个过程中,最深刻改变医学样貌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使用。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几乎同步的医学技术在过去的百年间特别是几十年间高速发展。它极大地提高着诊疗的能力。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新药、新材料面前,在人们对健康和医疗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在医疗取得很大成就的今天,人们自然地遗忘了那并未改变,也不可能动摇的医疗本质: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与此同时,可及性带来的过度诊疗、分科过细带来的局限、成本提高带来的高期望值和成本分担的压力…… 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全球性“医学的焦虑”,促进了对医学温度的呼唤。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回到过去,但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技术再进步也无法取代人对情感的需求,无法取代对病患的人文关爱。这是人性最底层、最根本的需求。当人承受疾病痛苦时,这种需求是最强烈的。更何况医疗技术并不能覆盖所有疾病,也无法对每种疾病、每个特殊的个体都能“手到病除”。在技术仍然也必将永远有局限的医疗领域,人文关爱才是永恒的。
因此,我们在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要为医学回归人文关爱做出努力。加强临终关怀的人文教育和建立安宁疗护学科,就成为北大医学部教学改革的内容之一。让人欣慰的是,北医系统内及兄弟院校有不少专家学者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借鉴国外较先进的理念和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支学术力量,形成了一整套临终阶段的医疗技术方法,并反映在医学教育的实践中,以及在职人员培训中。安宁疗护是完整医疗行为重要的一环,它是经过严格、科学、专业评估后,由患者及家属充分认同,放弃不必要的“侵入性”治疗,对终末期患者实施的一系列治疗,包括支持疗法、症状管理和心理救治。它不再追求以天计的生存时间,而专注于患者每一天的生活质量,它促进患者与亲朋的互动,给患者以安然告别的机会。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也让我们认识到,安宁疗护的推广普及,不仅仅是建立学科、建立实体机构的问题,还需要体制上的保证,需要模式上的构建,需要医患观念上的改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就个人来说,对医疗中安宁疗护的关注开启了我对生死问题的更广阔的思考,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造物主”赋予人类思考和探知世界的各种能力,却又让我们不知来处和归途,让我们的生与死都很被动,让我们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大脑,让我们看不到宇宙的全貌……作为芸芸众生的大多数,死亡之问留给我们的仍然是太多的困惑。人们或有惧怕死的贪生,或有不知死的“折腾”,更有茫然而导致的回避、苟且……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不同程度地在这几个层面徘徊。不过,这些年的阅历,包括读书、与同道的交流探讨和思考,让我在通往坦然的路上有了两个认知上的小进步:首先要追求活得更加豁达,努力做有益的事,注重健康、有爱,争取不被功利驱使。其次是死亡不可能避免,但善终可以追求。医学实践已证明,除了急性致命性伤害,人在慢性疾病的终末期,生的期限是可以通过专业评估,靠明确指标而预知的。很多对濒死者的研究也让我们可以想象和宁愿相信,当生命无法继续维持时,当生命放弃挣扎时,当生命接纳死亡的来临时,人类感受到的可能并不是痛苦,反而是欣快,不是黑暗,反而是光明。可是,这样的过程很容易被无知干扰和破坏。我理解的善终,是安心坦然、无痛感地离开。这需要我们在健康时就有理解,在疾病时早有准备,只有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配合医者帮到自己,帮到亲人。虽然我不能保证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至少有了方向,也更愿意继续探究和学习提高。
长期以来,国人是不愿和不能谈论死亡的。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直面这个问题,投入思考、分享见解、获取信念和信心。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观察、分析、论说。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可供参考的文献与活动、做法。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幸运地汇集了一批专家学者,其中既有医学人文教育专家,又有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还有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爱心,对生命高度尊重与敬畏,认真投入、砥志研思。当北大优秀校友黄怒波先生谈到拟在丹曾文化“人文·智识·进化丛书”中设立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内容时,我们一拍即合。即使不能对生死问题给出解答,我们也可以跳出医疗视野,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且深入讨论生死问题,把有可能想明白甚至有可能改善的部分尽力挖掘出来,使之广泛传播并召唤更多的人付诸思考与行动。
孔子弟子问:敢问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虽然我们的来与去并非自主,但生的过程仍极大依赖个人的选择。其实,“不知死”同样也不能更好地“知晓生”。我们谈论死亡,不光是为了追求善终,为了多一些坦然、少一些恐惧,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悟出该怎样更好地活。
希望通过努力,人们可以生而美好,逝而从容。
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