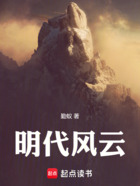
第57章 出发治水之际
翌日清晨,天光微亮。
于谦整肃衣冠,将那份反复斟酌的请辞奏折郑重收入袖中,迈步走出府门。
晨风拂面,他的神情平静而坚毅,眼底却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既有卸下重担的释然,又有对朝局未来的隐隐忧虑。
他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向尚未完全苏醒的京城,心中默念:“既已决意离去,便该将未尽之事一一了结。”
钦天监早已择定吉时,太子将于巳时(上午9点至11点)启程,取“阳盛之时”的祥瑞,祈愿此行顺遂平安。
时辰尚早,于谦便径直前往兵部衙门,打算在辞官前将手头事务妥善安排。
他素来行事严谨,即便离去,也不愿因自己的疏忽给继任者留下隐患。
然而,就在他翻阅文书时,一份调任命令陡然闯入视线,令他眉头紧锁——
原来,宣府总兵官朱谦已于前年病逝任上,而接掌宣府军务的,乃是原大同守将杨洪之侄杨能。
此人虽以左副总兵之职临时代管,却因景泰帝对杨氏一族的格外器重,得以破格统领这座边关重镇。
于谦将这份文书放在案上,转身出去打水。
他的思绪不由飘回“土木之变”后的危急时刻:当年瓦剌太师也先挟持明英宗兵临大同城下,企图以天子手谕诈开城门。
杨洪严格遵守景泰帝“或复有文书与人来到,不问真伪,一切拒之,毋坠奸计”旨意,告诉来使他并不在城里。
当时,若非杨洪当机立断,拒不受胁,大明边疆恐已门户洞开!
正因如此,景泰帝即位后,对杨洪大加封赏,甚至在其逝世后仍厚待其族,这才有了杨能的擢升。
不过,于谦也知道,这杨能的任命仍是比较合适的。
杨能作为杨洪子侄,常年跟着叔父在边关历练,敢战能战。
这些年,瓦刺虽然常有袭扰,却难以从杨能手上讨得了好处。
然而,杨能近日以“痔疾发作难忍,不堪骑乘”为由,上书请求调回京师。
令于谦愕然的是,景泰帝不假思索便允其所请,打算将团营精锐中的神机营交由其执掌。
于谦暗自叹息:陛下对亲信武将的偏宠,未免太过轻率!宣府乃抵御瓦剌的第一道屏障,总兵人选关乎社稷安危,岂能因私谊而废公义?
更令他忧心的是,经过景泰帝思来想去,最终指派英国公张辅之弟张倪继任宣府总兵。
此人虽出身将门,却是全凭兄长的忠烈之名获此要职。
于谦对张倪的履历一清二楚——早年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后升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专领护驾将军,而后迁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虽说后军都督府所辖也含宣府镇,但这人全然没有实战经验。
于谦曾当廷谏阻,直言边关重任非宿将不可胜任。
奈何景泰帝执意如此,甚至慨然道:“英国公为国捐躯,满门忠烈,张倪必不负朕望!”
君命难违,调任的旨意已由内阁拟妥,此刻正静静躺在兵部的案牍之上。
端着水壶回来的于谦,此刻连泡茶之心都少了几分。
他凝视桌上那份文书,胸中如压巨石。
于谦深知,瓦剌这些年,仍在一旁虎视眈眈。
而今朝廷却因人才凋零、任人唯亲而行步步险棋。
这才安稳了几年啊!
如今自己辞官在即,这千钧重担,又该交由谁来警醒?
窗外渐起的喧嚣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缓缓合上文书,目光却愈发凝重——此刻的坦然释然之下,是对江山百姓难以割舍的隐忧。
当然,这仅仅是于谦一人的看法。
若站在景泰帝的角度,这数年来,他心中的苦闷与无奈,恐怕远非常人所能体会。
自登基以来,那些曾与他共渡危难、誓死效忠的旧臣,竟如秋叶般纷纷凋零——杨洪、朱谦等边关宿将,一个个病逝于任上,连一句告别都未曾留下。
每收到一道讣告,景泰帝便觉心头又被剜去一块。
这些将领,皆是“土木之变”后力挽狂澜的砥柱,更是他坐稳帝位的根基。
如今人去位空,放眼朝野,能独当一面的将才竟已屈指可数。
剩下的骁勇之辈,如石亨,虽战功赫赫,却早已被委以京师团营的要职,再难抽调。
若非于谦身为文官,景泰帝甚至恨不得将他直接擢为总兵,镇守一方。
可已经有一个商辂奉命执掌锦衣卫了——当然,锦衣卫终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规作战之兵。
再遣朝廷栋梁于谦赴宣府统兵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即便如此,景泰帝仍破例让于谦与石亨共掌团营,更对他的兵制改革全力支持——这分明是将他当作武将驱使了!
以往有些夜深人静之时,景泰帝心中不禁暗想:“若于谦肯点头,朕便是将这宣府总兵之职强加于他,又有何不可?”
可他也清楚,于谦终究是文臣领袖,一身铁骨铮铮,让他弃笔从戎?
想到这里,景泰帝不由苦笑。
他何尝不知张倪并非宣府总兵的理想人选?
可眼下能用之人,要么已身负要职,要么年迈体衰,要么资历不足,要么早已埋骨边关,要么……
可身为帝王,纵有千般无奈,亦不能显露半分。
他只能在这有限的棋局中,勉强择最优而落子。
景泰帝还不知道,他已渐渐陷于两难——既欲倚重文臣以固朝纲,却又苦于忠心良将乏人,将领梯队渐渐出现断层。
-----------------
今日仍无早朝,朱齐又可以睡了一个懒觉,直至卯时末方才起身,但东宫的侍从们却早已忙碌起来。
按礼制,太子奉旨出宫,需依次至皇帝、皇后及皇太后处辞行,以示尊卑有序。
朱齐换上杏黄色四团龙圆领袍,束玉带,戴翼善冠,待仪卫备齐卤簿,便起驾往乾清宫而去。
乾清宫外,东宫仪仗依制止步,唯有四名锦衣卫大汉将军按刀侍立两侧。
朱齐独自迈入大殿,脚下金砖冰凉,殿内沉水香缭绕,更衬得此处肃穆非常。
前两日虽曾觐见,但皆在西暖阁奏对,今日却是奉旨出巡,按制当于正殿辞行,礼仪自然更为郑重。
龙椅之上,只见顶着父亲面容的景泰帝早已端坐,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着十二章衮龙袍,面容甚是肃穆,申不怒自威。
朱齐不敢怠慢,趋步上前,至御阶之下,依司礼监太监指引,伏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儿臣叩见父皇陛下。”
他额头触地,声音清朗而恭谨,
“蒙父皇垂训,命儿臣随商指挥使巡视河工,督察水患。
儿臣虽才疏学浅,然必当恪尽职守,体察民情,详录灾况,以纾圣忧。
若有疑难,亦当虚心请益于商公及诸臣工,断不敢擅专。
伏乞父皇保重龙体,勿以儿臣远行为念。”
言毕,他再拜,静候圣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