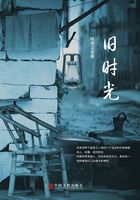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川剧缘
我与川剧“结缘”怕已有五十年。
儿时就极喜川剧,家贫无钱难进戏园,古镇亦少来戏班。偶尔来之,便伙同一帮细娃爬上剧场高墙那五角星的大木窗,抓住条框,脖颈伸长往台上望;偶或也有躲在拿票的生人腋下,低头缩身朝里拱的劣迹。胆战心惊混进,进去再朝台边挤。踮着脚尖,吊住台沿仔细看,眉毛胡子都真切。那时我最怕大花脸,声如洪钟,面似厉鬼——实为极富审美价值的脸谱——吓得我直往地下缩,怕他那马鞭挥打到我的瘦脑壳。
越怕越看。看吐火,看变脸,看剧中的离合悲欢,听唱腔的悠扬婉转,欣赏川剧的魅力无限。仿佛穿越历史隧道,借以暂时忘却儿时人生的苦辣辛酸。
可这样的机缘很少。偶遇到的是谁家办红白喜事,请一帮川戏“发烧友”晚上到办事人家门口“打围鼓”,亦叫“唱玩友”。川剧家什在古镇石板街一溜摆开,汽灯挂在翘起的屋檐角或干枯的树枝上,滋滋着响,把小半条街面照个通亮。倘是雨天,雨丝的根根银线都照得极其明显。左邻右舍着厚衣夹袄,慢腾腾踱来。抄手缩脖,或坐或站围成圈。玩友的锣鼓唢呐很齐全,先试锣鼓,再调胡琴;弄出动静,吊住人心。待看客安定,猛然一通紧锣密鼓,川剧帮腔拔地而起,高亢清越,哀转久绝。道白纯正,亦有情节。其对唱,更是如泣如诉,声嘶力竭。众人或张嘴痴望,或哼着节拍,或闭目击节,全不顾寒风凛冽。夜间空气颇新鲜,加之屋内咿咿呀呀地哭,令人感慨系之,别生一番思人的情绪。
那时家父尚在,他平时亦爱哼两句。手把茶壶,微闭双目,摇头晃脑,旁人全无:
“手挽手儿过山腰,尊一声我的老伯父,细听根苗……”
父亲还比划,那神情非他最高兴时不能见着。而唱词何意?归哪出戏?我至今不晓得。
我有位在武胜县川剧团唱旦角的本家。怎么攀上亲的不知道,总之我该叫她“陈嬢嬢”(即:阿姨)。其实陈嬢嬢也就二八上下,亦从未到过我家,我倒是从内心着实荣光了好一阵。每当剧团来古镇,而我父母又没钱给我买票,我又在戏园门口站麻了脚,且戏将终场的时候,我便敢“麻着胆子”气而派之往里走。守门的拦住我,我咬着小指母歪着脑壳说:“我嬢嬢在剧团里头。”
“谁呀?”
“陈淑华。”
守门人笑了,拍着我的小脑壳开门放我。
我得意非常。
有次我竟贸然溜进后台,看演员卸妆,看他们进退场,感觉实在风光。
有顷,陈嬢嬢飘然下场。穿着戏装。裙幅垂拖,娇美婀娜,胜过月宫嫦娥。我激动而怯怯地叫了声:“陈嬢嬢”。想象她定会惊喜飘来,放下身段拉我交谈。
陈嬢嬢优雅转身,我心将迸出。
陈嬢嬢款款而至。目眶冉冉,姿态翩然。却极陌生地看着我,清美柔和的问我。——她不晓我是谁家娃,更不认识我这小本家。
我鼻酸泪下,结结巴巴答。陈嬢嬢大眼扑闪,思索半天,浅笑遗憾——人家根本不知我的父母为谁何,更不晓得我们这门亲戚的来龙去脉。但陈嬢嬢还是蹲下细腰给我擦去鼻涕,还留我吃了顿夜宵——猪尾脊骨炖大青萝卜。
事后我不知给多少细娃妹仔吹过壳子,似乎自己亦由此长大了,对耍泥巴的小伙伴颇有不屑一顾的味道。
二十几年后我从新疆回老家,将此事于酒桌跟亲戚聊起,几增唏嘘。一亲戚言他熟悉陈淑华,早退休,前两天在菜市还见着。热忱说:“她要知你去,不晓得有多欢喜。”便要饭后领我去。我很想去,可返四弟家的车票已买;更怕再见陈嬢嬢与儿时所见彼此反差的迥异,反倒破坏了当年美好的记忆。所谓“相见不如思念”,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我以我的没去拜访本家嬢嬢而心生愧意。
记得刚上初一,嬢嬢所在的县川剧团来中心中学招生,我又兴奋了好些天。臆想我多年参加“镇宣队”,主演过儿童“样板戏”,也算“小有名气”,考试录取估计无问题。结果是我班的屈八儿、何二妹走了。真羡慕得难受。不久,我又因生计而离乡万里,一去便是二十载有余。再没听过蜀腔,更没看过川戏,亦不知考上剧团的小伙伴的消息。
1991年我回南充探母,才晓得县川剧团早已解散。屈八儿做了缫丝妹;何二妹成了个体老板。我很想去探望,与她们畅聊川剧,叙谈儿时的友谊。好易寻至屈八儿家,她早无昔日李铁梅的影子。整天劳作于车间,疲惫不堪。未开几句言,便匆忙别过去上夜班。曾经娇小灵秀的川剧演员再没唱戏之意,更无谈戏的兴趣矣。
我寄希望于南充市川剧团。然而川剧场地成了录像大厅,老放些俏女鬼神怪侠片,以此来维持其艰难生计。
我决计要走了,返回我遥远边疆的谋生地。娘亲、四弟竭力留,我还是买了火车票,打算翌日离蜀川。当我最后一次到南充剧场门口逗留以作告别时,川剧广告竟赫然入目。我欣喜若狂,老早就催促四弟同去买票。而窗口紧闭。等出位靓女,川剧演员无疑。打听,她说:
“你们来看就是。包场,不卖票。坐不满的。”
“坐不满还不卖票?”
“是啊。”她美目盼兮,看我亦怪怪的,似乎不明我问话为何意。
而我实实感到悲哀,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人疯狂地去追这腕那星,将大把鲜花和金钱为他们抛洒,却无意扶持我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连老外对我传统戏曲都喜爱有加,而芸芸国人却莫名其妙,不知云何……
是艺术的悲哀,还是国民素质的低落?——得由后人说。
那晚的川剧,演得真好。可场内木椅大多是空的,像一个个高耸的墓碑。
我说不出话。
第二晚还有,然车票已买,我只得别情依依告别了南充,告别了川剧,心里歉歉的。
1993年底,我调至攀枝花市,其吸引我之一的就是这里能常看到川剧。每星期都有一场。攀枝花市川剧团水平颇高,劳累一周,买张戏票去看戏,真是优雅之极,快乐之极,享受之极。倘再肯花一元钱,泡碗清茶和着戏味慢慢品,更是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其中妙处唯我自知。我每场必看,且坐前排。常常是观众都已往外走,我还盯着那枣红的幕布不愿离去——那里面有好大好神秘的艺术天地哟!
我的川剧缘,今生今世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