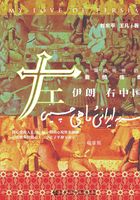
岳母为余粟解了围
大客厅里越来越热闹了!亲戚朋友和宾客们陆续到来,几个房间里人越聚越多,人头攒动。岳母大人告诉余粟,今天到场的一共有150多位。
此时,哈梅德的父母挽着女儿女婿,穿过客厅,来到家中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此刻已然布置成了一个婚礼仪式的“殿堂”。
房间摆满了鲜花礼品,中间安置了新郎和新娘的座席。座席边上,放着一本精装的《古兰经》;还有一只盛满蜜汁的高脚杯,两枚扎着白色蝴蝶结的糖棒(蜜蜡棒)。这些,是举行结婚仪式上必不可少的物品。
靠墙边上,还摆放着一面古色古香、工艺考究的铜框大镜子和两架铜烛台。通过前文所摘引的《忠贞不渝的爱》中的片段,我们已经知道摆放这两样东西意味着什么。
前来贺喜的亲友们按照长幼亲疏秩序,依次来到新郎新娘座位前,将准备好的礼金送到新人面前,或把金项链、金戒指、手表、手镯等赠礼亲自为新郎或新娘戴上。哈梅德的妹妹身背一只布袋,站在姐姐姐夫的旁边,代他们收纳亲友的礼金、礼品。
送礼环节之后,在至亲好友的围拢中,由哈梅德的两个妹妹一左一右,在新人座席头顶上方撑起了一块约2米的长方形白布。另一个小妹妹和女伴站在白布边,各执一只糖棒(蜜蜡棒),在白布上吱呀吱呀地磨搓起来,白色糖粉(蜜渣)便纷纷扬扬洒落在新人头顶的白布上,这象征新婚夫妇沐浴在甜蜜之中,生活像蜜糖一样甜美。
接着,另一位女宾把高脚杯举到新人面前,两人分别用小拇指,在高脚杯中蘸满蜜汁,送到对方嘴中。两位新人都张开嘴,几乎把对方的整个手指吮进嘴里。因为其间也有着美好的寓意:吃到的蜜越多,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越幸福!
在伊朗,有一部名为《我在伊朗长大》的漫画小说,被译成了15种文字,受到世界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后,更是蜚声全世界。在《我在伊朗长大》的叙事中,也有对余粟亲历的伊朗婚礼一模一样的场景和细节描写。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互换婚戒的环节。余粟取出他悄悄带在身上的金戒指,戴在新娘的左手无名指上亲吻;哈梅德也同样含情脉脉地将一枚她精心挑选的婚戒,戴在新郎的左手无名指上,亲吻。
余粟觉得,在伊朗行互换婚戒礼仪的意义非同寻常。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知道了这个如今在全世界通行的结婚礼俗,就发源于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伊朗,发源于波斯古老的拜火教。
拜火教崇拜的最高神灵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就是左手握一金圆环的长者,他手中的圆环,即代表着契约精神与承诺。
在古波斯时期,帝王之间签订协议时,双方都要交换金环,以此做为重承诺、守信义证物。后来,民间结婚仪式也广泛效仿这种形式,圆环逐渐演变为象征男女双方共守婚姻戒约的婚戒。佩戴在左手无名指,意味着左手连心,心心相印。
这时,哈梅德的母亲玛利亚将一对金耳环,放到了余粟手上,示意余粟为她女儿戴上。哈梅德连忙附在余粟耳边,快速说了句:“千万别一次就给我戴好啊。”
对哈梅德的嘱咐,余粟感到十分纳闷:给女孩子戴耳环不是很简单的事嘛,为啥还不让一次就戴好呢?
可尽管余粟不是有意为之,由于被周围那么多双热情的眼睛注视着,再加上置身异国他乡突来婚礼引起的紧张情绪,他在给哈梅德戴耳环时才注意到自己的手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真的半天没能找准新娘的耳朵眼儿。
正当余粟满头大汗地来回揪扯哈梅德耳朵时,一双胖乎乎的手握住了他的手,帮他把一对耳环为哈梅德佩戴好了。原来这是岳母大人的双手,是她在最需要的时候,帮了余粟一把。见美丽的新娘带上耳环后,全场为之报以热烈的掌声。
余粟一时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戴个耳环,还要热烈鼓掌呢?后来他才明白,伊朗人很善于用一些生活中的细节,来寓意和表达他们的一些传统习俗和观念。
就拿戴耳环这个小环节来说,如果新郎一下就把耳环戴进新娘耳朵眼里,就表明新郎很有性生活经验,新娘也可能不是处女之身了。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就会嘲笑议论这对新人,认为新郎是个花花公子,认为新娘生活不够检点等等。如果这耳环戴得缓慢,或反复几次才戴好,亲戚们就会认为这对新人很纯洁,这个家庭是个有教养、懂规矩的人家,父母和家人的脸面上也就有了光彩。
虽说在余粟看来,今天西方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些年轻人早已接受了例如男女恋爱中的试婚、伴旅等做法,而伊朗人仍固守和秉持着一如20世纪之前传统中国人遵循的操守观念。这一切,没有亲历的感受,是不可能有深切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