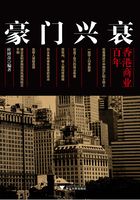
第7章 船王和他们的时代(2)
赵从衍、曹文锦也许应该感到庆幸,最终留在了香港,而不是返回大陆。1949年和他们一同避居香港的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在1950年带领旗下轮船回归大陆,一时间,各种头衔接踵而至,好不风光。可惜两年后,49岁的卢作孚便吞食安眠药自尽,而那时,民生公司早已换了姓氏【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突破英美日轮船公司的重重封锁,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大陆解放后民生公司被收归国有。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解放前后,民生公司旗下船只多达150余艘,员工近万,卢作孚号称“船王”,到头来人财两空,悲剧收场,在同时代商人中引起怎样的震颤?相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慨留在香港的赵从衍、曹文锦又是何等幸运?他们在香港构建起自己的航运帝国,还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亿万富翁,家族繁衍旺盛。
然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非但当时难以预料,就连日后回首,也不免徒生怅惘。
赵从衍、曹文锦将生意与资产留在大陆,摆在他们面前的谋生问题日益突出。好在商人总不缺办法。
由于美台施行经济封锁,大陆解放伊始进出口贸易十分疲弱,为了换取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专门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贸易港。曹文锦得知这个消息,与几位朋友租借了一艘货船,将大陆的猪鬃、大豆、桐油等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或到日本换成国内急缺的钢材、化工产品。日本战时工业过剩,战后堆积大量钢材,价格低廉,但农业生产萧条,对粮食需求旺盛,刚好与中国大陆存在贸易互补。曹文锦利用需求关系,来往与山东、香港和日本之间,从1949年开始,短短几个月,便赚了几十万港币。用这笔资金,他们创建了大南轮船公司,即万邦航运前身。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一艘从新加坡购买的超过40年船龄的1200吨货船。【参见《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不久,一个更大的机会到来了。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施行禁运。作为美国盟友,英国虽公开声明对华禁运,但港英政府却“执行不力”,一直默许民间走私的存在。因“禁运”导致中国大陆与北朝鲜物价飞涨,运费水涨船高,每吨运价竟高达150美元,利润堪丰。
这一时期,曹文锦采购药品、钢材经澳门运往大陆,但唯一的那艘货船在经过汕头海域时,被国民党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不得不斥资100万港元,购入一艘3600吨级旧船,“运载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往内地,并兼做出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引自何文翔著:《香港富豪列传》,明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很快又从买入两艘400吨旧船。
与此同时,赵从衍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赵从衍雇人在香港揽货,用唯一的那艘旧船“国兴号”运往北朝鲜。他在香港创办的华光航业公司也因此枯木逢春,日进斗金。
非常态的市场中,风险与利润成正比。赵从衍、曹文锦均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与所赚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随后,二人不约而同地及时收手,开辟日本航线。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在朝鲜战争拉动下制造业兴盛一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但日本资源稀少,生产资料严重依赖进口,航运业变得有利可图。不过,日本本国船只在太平洋战争中毁损严重,当时十分匮乏轮船,许多日本商人、企业跑到香港租船,客观上刺激了香港航运业的繁荣。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批经验丰富的船工从大陆逃难到香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宁可接受微薄的薪水,使得香港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赵从衍、曹文锦大肆收编旧轮船,扩大规模,组建起各自的船队,日本运送货物,赚到“第二桶金”。朝鲜战争结束后,赵、曹两家以迅猛声势出现在香港航运界,成为战后新生代的代表。
董浩云拨云见日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正当赵从衍、曹文锦辗转腾挪之际,董浩云陷入万分艰难的局面。
董浩云来港不久便将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业公司迁往台北注册。当初他从大陆撤离时,中国航业公司旗下船只被国民党军规征用向台湾运输军火物资,还有几艘正远航欧美,所以董浩云手中实际上只有复兴航业公司三艘美国货轮,并且还负担着美国银行沉重的购船贷款。1950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美方以“欠债未还”为由,将复兴航业公司旗下“京胜号”、“沪胜号”两船扣押。董浩云顿感灰心:“老旧船只无力做新陈代谢之谋,现有吨位亦逐渐锐减,遂使无依无靠之中国仅有少数民营海运事业,几处岌岌可危的境地之中。”【引自董浩云长女金董建平与郑会欣编著:《董浩云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1版)一书P76所载董浩云在1953年11月撰写的文章《历尽沧桑话航运——廿五年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回顾》】
仓皇之间,董浩云将仅剩的一艘货轮“渝胜号”紧急移往香港,注入到香港注册的分公司“金山轮船”名下,他还将船头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换成米字旗,希望摆脱美国人的视线。
几个月后,朝战爆发,美方出于战略考虑,与台湾方面修复关系,并把“京胜号”、“沪胜号”完璧归赵。董浩云大喜过望,将两船注入金山轮船公司,以香港为大本营,加入战时航运之列。“京胜号”、“沪胜号”、“渝胜号”三轮具有显著的特征,船体一律漆成灰色、烟囱则刷为醒目的黄色,上有梅花标志,出入维多利亚港,很快就成为金山轮船公司的标志。
不过,太平洋闹船荒,台湾国民党交通部紧急征调董浩云旗下所有船只,为美军一方运送战争物资。由于这种关系,董浩云在亲美的日、英、法等国订购船只、开设分公司颇为顺利,这一优势一直持续到战后,是许爱周、曹文锦、赵从衍等人无法相比。而董浩云也很聪明地利用了这种优势,从英国订购万吨巨轮“瑞云号”与“太平洋光荣号”客轮,事业重见天日。【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91《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航业公司、复兴航业公司解除监理,被征用的船只陆续归位。与此同时,借助国民政府的支持,董浩云竭力增购船只,扩充船队规模,日渐恢复元气。
为了适应能源运输的需要,董浩云不惜巨资订购巨型货轮,与前身是日本海军造船厂的“佐世保重工业株式会社”建立了固定合作关系。1955年,该公司协助董浩云改装“太平洋荣誉号”油轮,使之适用石油、矿砂的运输需要。第二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石油运价大幅攀升,董浩云又从佐世保重工订购11000吨石油、矿砂多用途货轮,即1958年下水的“大西洋信仰号”。此船下水半年后,7万吨超级油轮“东亚巨人号”即在佐世保开工,于1959年底交付,随即被日本“东亚燃料会社”租用。
195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批准董浩云的造船请求,并向“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提供政府贷款,建造两艘1.25万吨客货两用轮“如云号”、“复安号”。这一次,造船合同再次交到日本人手中,由住友重工旗下浦贺造船厂承造。日本造船业的速度再次得到证明。“如云号”一年后下水,刚好赶上董浩云创建“东方海外”,成为“东方海外”中美航线的首航客轮。【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93《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一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是,董浩云的航运事业得到台湾方面的扶持。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航运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发展航运业的重担则落到董浩云身上。他多次到台北接受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政要接见,还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航业公会事务,获得台湾政府或美国银行界的巨额贷款,有财力订购船只,扩大规模,在世界各地开设分公司,开辟新航线。
进入60年代,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进步,西方航运大国掀起一股汰旧换新的热潮,给了董浩云扩编船队的绝佳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就是购买美国的胜利型货轮。
60年代初,董浩云以100万美元的总价从美国一次性购入12艘胜利型旧船。按照当时的汇率,平均每艘轮船折合港币仅50万元上下,相比动辄数百万美元的新船造价,显然是极大的优惠。要知道,包玉刚1955年从英国购入那艘8700吨旧船“金安号”便耗资70余万美元。胜利型货轮与“金安号”排水量与此相当,船龄也相差不多,价格竟如此便宜,几乎等同白给。
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借此向董浩云曲意示好,弥补当年扣押“京胜号”、“沪胜号”对其造成的损失。如果美国人有这方面的考虑,也一定是附加因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批船对美国人来说已经落伍了。胜利型轮船建造于二战时期,到了西方造船业向自动化高歌猛进的1960年代无异于“老古董”,欧洲人、日本人都不会买这些旧船,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急于发展航运的台湾,于是借淘汰装备的机会,顺便给了董浩云一个大便宜。
对此,董浩云自然心知肚明。不过,以生意人的眼光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胜利型货轮虽然船龄已久,存在耗油量大等缺点,但质量可靠、耐用,承担货运绰绰有余,增加的油费成本可以通过调整运价来弥补,况且香港船员薪酬低廉,人力成本也可以弥补油费支出。
生意人不做赔本买卖。董浩云精打细算一番,认为这笔交易于己有利,并不在意轮船新旧。后来,他创造性地把这批旧船从散装货轮改装为货柜轮船(集装箱),就此转向效率更高、利润更大的货柜运输,为“东方海外”的主营业务——货柜航运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这12艘胜利型旧船在1970年代退役,它们在董浩云手中居然又用了10年。
包玉刚后来居上
包玉刚是航运四子中最后一名入行者,却是起点最高、成就最大的那个。这或许与他的银行从业经历不无关系。
1956年,环球轮船成立第二年,包玉刚赢得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桑达士(Saunders)的信任,从汇丰银行获得一笔贷款,订购6艘货轮,仅仅一年,包氏旗下船只便增加到7艘。
在此之前,汇丰一直坚持“不借贷给轮船公司”,尚属无名之辈的包玉刚何以令汇丰为他破了戒条?
原来,包玉刚并不像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那样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将轮船出租给有需要的航运公司。这样一来,不必承担航运各种风险,经营压力骤然下降。
到香港租船的主要是日本人。二战时日本船只几乎损失殆尽,造船工业也遭致沉重打击。到195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进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大量货物待运,船只需求量猛增,但日本人拿不出去钱去订购新船,只得租赁。与此同时,香港航运业“有船无货”,大批轮船闲置,刚好与日本“有货无船”的状况形成互补,双方一拍即合,建立租赁关系。
轮船租赁严重制约日本造船业发展,各大船厂无米下锅。为扶持本国造船业,鼓励国外订单,日本银行界向外国船商提供购船低息贷款,利息甚至比给本国人的还要低。这样一来,对于日本船商而言,买船远远加不如租船划算,因而加剧了租船力度。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厂订制新船,然后就地转租给日本的贸易公司。所以后来人们常说,香港航运业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并非毫无道理,起码在早期是这种关系。
包玉刚入行时,轮船租赁在香港已习以为常。他拥有的第一艘轮船“金安号”就租给了日本人,这一点并没什么特别,但他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格长期出租,这就不同寻常了。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正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让他赢得了桑达士的认可,最终帮助包玉刚敲开汇丰银行的大门。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将轮船长租出去,这样收入虽然不会很高,但稳定可靠,平均利润也不少。
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汇丰银行从前之所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向轮船公司放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运业受政治、气候、战争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致使稳定性不足。现在,包玉刚通过与承租者联合分散风险,找到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不愿错失发展先机的汇丰银行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汇丰方面要求包玉刚提供租赁方的银行信用担保。这难不倒他。
包玉刚坚信,商业是一项双赢的博弈,不仅要以信取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对方从合作中获利。因此,在租赁合约上,他一再作出让步,不但事无巨细地划分责权,甚至承诺如果轮船出事,保险赔偿金将全部归租赁方所有。就这样,包玉刚总能如愿拿到租赁方的银行担保书,以此从汇丰贷款,再以贷款合约去日本造船厂签订造船合约,用“三张合约”开启了航运帝国的大门。
每一名创业者未必都能品尝到收获的喜悦,但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开拓的艰辛。包玉刚也不例外。据曹文锦回忆,那时候为了招揽日本航运生意,包玉刚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启德机场守候日本客户。一群香港船主围在出口,看到日本人模样的人,这些平日文明的同行便顾不得斯文,纷纷涌上去争抢客户。曹文锦注意到,包玉刚也在其间,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去争夺客户,而是认准一个客户,一把抓过对方行李,径直就走,对方为了拿行李,只好乖乖跟他走。包玉刚善于抓要点,让问题迎刃而解,曹文锦便偷学了这招,竟也屡试不爽。
包玉刚认为,“船东的经营原则,根本上就是经常要维持最低成本”。只有这样,租赁方和自身才能从中双赢收益。有一次,“金安号”在驶往日本长崎途中发生故障,被拖往长崎修理。包玉刚闻讯后亲自赶赴日本,监督整个维修过程,确保每一笔开支到位,令租赁该船的日本公司大为佩服。